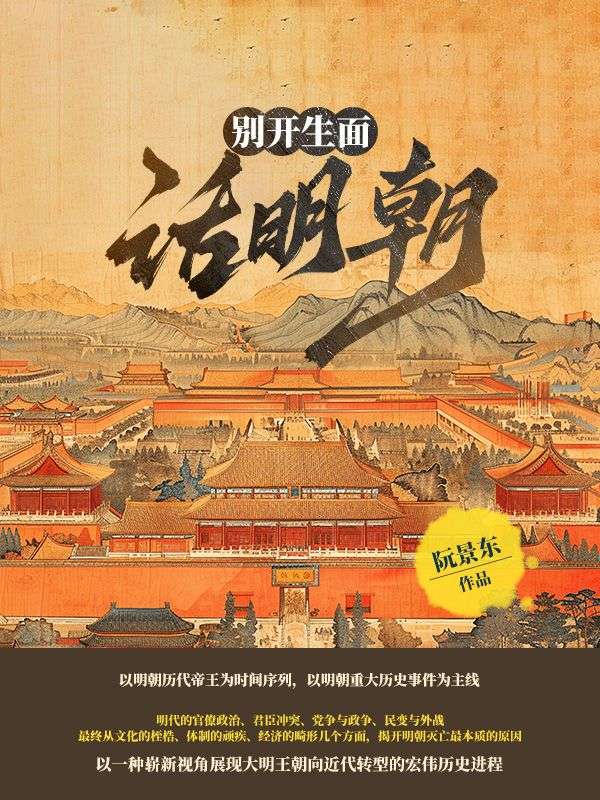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19 妖言惑眾的朱季友
19 妖言惑眾的朱季友
曆史上總有那麼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朱棣進入南京後對儒生大開殺戒,隨後他搖身一變成了大明王朝最大的衛道士。曆史上也總有那麼些玄而又玄的事情,雖然不為任何人所懂,但它一直能占據統治地位。這一節我們就來介紹在整個明王朝占據官方統治地位的思想——理學。
東周時期王室衰微,群雄崛起,每一個諸侯都想一統天下,但保守而虛偽的儒家思想顯然不能在這個過程中起到作用。法家思想能夠使一個國家高效率運轉起來,調動幾倍於他國的資源來進行戰爭。但法家思想是治吏,而且會影響到中產階級的利益,所以向來是受抵製的對象。儒家思想是限製君主的權力和治民,它維護的是士大夫的利益,這些理由成了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推崇儒家思想的最本質原因。秦國地處中國的西部蠻荒之地,它的意識形態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張白紙,這才是法家學說能夠在秦國得以實踐的原因。秦一統天下後,法家思想的邊際發展效率卻越來越低下,最後卻不容於這個古老的農耕帝國。法家思想本身並沒有錯,隻是在執行中出現了偏差,根子在商鞅和韓非時代就已經種下了,兩人在設計法家理論時賦予了一些僵化的因素,反而沒有關注更加本質性的東西,最終是束縛了自己的手腳。
大漢開國後麵對民生凋敝的局麵,幾代君主皆采取休養生息的政策,到了武帝時代為了打擊匈奴,宣帝時代為了抑製豪強才重拾法家思想,此時的法家思想已經比先秦的法家思想要圓潤的多。
東漢時期道教興起,到了魏晉又興起了以清談為主的玄學,隋唐興起了佛學,一直到宋代,儒學才以理學的麵目正式登入政治舞台。儒家思想曆經1500年最終還是以一種變異的形態才取得官方的正統地位的原因究竟是什麼?
哲學體係裏有一個叫本源的問題。我為什麼要吃飯?因為我要活著。我為什麼要讀書,因為我要明是非。儒家思想主張行仁政、禮治,但對於為什麼要這麼做卻沒有做出解釋。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這反映了儒學對終極問題的回避。這一方麵是因為儒家思想理論上的缺失,但究其深層次的原因乃是儒家思想的膚淺性,更多的隻是一些經驗上的總結,由知識分子將這些經驗上的總結以極其霸道和不厭其煩的方式推銷給統治者。
思想領域你不去占領,別人就會占領;你不能解釋的東西,別人就要來解釋。
道家思想、玄學思想和佛教思想都對這些本源性的問題做出了解釋。道家思想將人類的一切終極問題都歸於道,玄學歸結於無,佛教將這些問題歸於空。但無論是“道”、“無”,還是“空”,都是一些玄而又玄的東西,也許理論的最初創立者也解釋不清楚,隻好弄一些抽象的概念來遮掩。到了宋代,理學終於登上曆史舞台,理學開始用“天理”來解釋一切本源的問題。理跟道與空比起來似乎更是玄幻,但無論如何儒學終於對本源有了解釋,也正是因為對終極問題有了回答,所以到了宋代儒學才第一次占據正統學說的地位。儒學新的表現形式理學被定義為官方的指導思想。
儒家思想是擴張性的,同時也是韌性的。它不似道家思想那麼獨善其身,也不似法家思想那般脆弱。千百年來中國的儒生們挖空心思的重塑儒學體係,這才有了以理學為代表的體係。到了明代理學仍舊是官方指導思想,這一舉措在永樂時代被大大強化了,官方對於儒家經典嚴格的按照朱熹的注釋進行解釋。
雖然儒家思想奪取了正統學術地位,但發端於東周時期的孔孟思想已經不適宜於本朝的思想環境。孔孟生活的時代已經遠去,禮樂早已崩壞,井田製、分封製也早已瓦解;西漢為了適應統治階級的需求,儒生們在儒學中加入了天人感應;到了東漢年間,同樣是為了迎合統治者的需要,儒生們在儒學中加入了算命的內容;再加上經過秦始皇的焚書,儒家原樣的書稿早已消失,後代的儒學書籍全部靠漢代儒生憑記憶默寫,可以預見的是在這種默寫過程中會存在這樣那樣的遺漏與錯誤。由此我們可知中國的儒學體係早已散亂化,不成章法,失去了它的原旨主義,到了本朝已是重塑儒學體係的時候了。
朱熹對於儒家經典按照自己的思路進行了重新解讀,無論他是有意為之還是無意為之,抑或是斷句和自身學識上的局限,這種解讀對於我們的文化典籍來說都是災難性的。可以明顯的看見他對儒家經典的解讀有意向三綱五常、封建禮教方麵引導,從此一個開放、博大、情愛、血性、舍生取義、大爭的儒學思想被閹割了,呈現在我們麵前的是一個裹著小腳、步履蹣跚、封閉萎縮的理學思想。
或許這種理學思想更適合統治者的需要,更適合宋明這樣保守政權對於思想文化的鉗製,更有利於結束五代和元末的散亂局麵,來重塑民族和國家的凝聚力。
雖然理學思想登台了,但中國思想文化的巔峰時代已經過去。我們已經無法看見先秦百家爭鳴的哲學思想、秦代自信的法家思想、兩漢精深的道家思想、魏晉詭辯而清談的玄學思想,我們所見的隻是狹隘、封閉、敏感、扯皮的理學思想。中國的士大夫們奮鬥了1500年才換的儒學以這種變異的模式榮登寶座,不知道遠古的這些大儒們作何感想?
在理學的倡導下,明初一些士大夫死後竟讓妻妾殉葬,這股殉葬之風竟然刮到宮廷。但曆史上總有那麼些個有識之士,能夠在沉悶的氣氛中發出令人振奮的聲音,這樣的人國末有一個——李贄,國初也有一個——朱季友。
朱季友是江西饒州府人,一位七十多歲的老儒生。朱棣要修書,需要天下的士子們將藏書或者個人著作交出來,這位叫朱季友的親自趕到南京將所著之書交了上去。朱棣看後勃然大怒,原來朱季友所著之書對理學提出異議。這的確是帝國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一件非常大的事。在那個程朱理學統領一切的時代,在那個所有讀書人都要按照朱熹的解釋來對儒學進行朗讀的時代,在那個科舉考試不能超出《四書》範圍的時代,朱季友的言論無疑於屬於異端學說,無異於在思想文化沉悶的大明王朝響起一炸驚雷。
朱季友究竟寫了什麼我們已經無從知曉,因為他所著的書皆被焚毀,本人也被杖一百。通過這件事情朱棣發出了一個明確的信號,那就是所有的行為規模、倫理道德都必須在理學的指引下。這個事件也使得理學正式成為顯學,跟理學所對立的學說成了隱學,隻能在地下發展。
當一個時代的知識分子所作的書竟以《焚書》、《潛書》來標榜的時候,我們隻能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這個時代,甚至這個王朝很多東西都離真理很遠。無論它如何一直努力前行,實際上隻是在原地打滾,甚至倒退。
但無論如何理學的出現是中國思想界具備裏程碑意義的大事。它解決了儒家思想關於世界本體論的問題,使得儒家思想更加完善,續接了儒家的道統。它注重道德,講究仁、義、禮、智、信,這些都體現了理性的原則,它注重對世界本源性的解釋,這又體現了一種思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