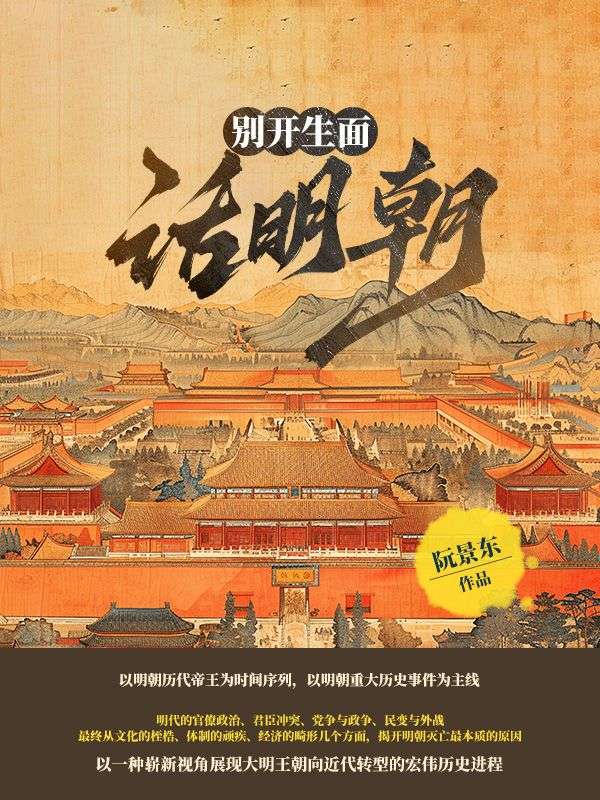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跋
2006年7月我從武漢大學金融係研究生畢業,就職於某地銀行一線。三個月的銀行實習生涯對我的確是種折磨。三個月後,我辭去銀行工作,後又經輾轉與逼仄,就職於家鄉一所中職學校教授曆史與電商學課。就這樣,與金融業漸行漸遠,而與曆史卻漸行漸近。
在我畢業後的兩年,正是網絡明史學派對明史進行顛覆與重構的兩年,各種創新觀點深深地吸引了我。傳統史觀將明朝描寫的黑暗與專製,但讀《萬曆十五年》,我發現皇帝不上朝是因為製度很完備。例如英國女王和日本天皇也不上朝。明代皇帝重用宦官是因為明代本就兩套官僚係統,一套文官係統,一套宦官係統。所以,重用宦官應該被當做曆史本身來研究,而不應該摻雜個人色彩。
黃仁宇的大曆史觀對我產生深刻影響。它使我知道,原來曆史也可以這樣解讀。對於曆史,我們應該拋棄個人先入為主的印象,要多去問為什麼?要深挖曆史背後的因果。不要被表象煽動情緒。這樣解讀出來的曆史,才更接近客觀事實與真相。杜車別對明史的解讀更是驚世駭俗。他認為明朝滅亡的原因是由於在技術條件達不到的情況下,超前發展所造成的。政治製度過度民主化,經濟體係過度商品化,這些都衝毀了明代統治的根基。
但黃的論述有些雲裏霧裏,不是那麼直接與簡潔。而杜的觀點則有些狹隘與偏激。例如,黃仁宇認為中國傳統社會以道德代替法律是一切問題之根源。但事實是,中國是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大部分人都生活在鄉村的社會。對於這樣的一種社會,用道德來管理的確比單純的法治更優越。而杜車別一再強調,明朝的滅亡跟萬曆與崇禎沒有關係,但明朝的滅亡的確跟萬曆與崇禎有關係。
後又經我自己研究,我發現了一些別人沒有挖掘,或者說已經挖掘,但還沒有被主流史觀注視的東西。比如明朝的啟蒙運動、異端思想、人文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工人運動、市民運動、充滿柔性的資產階級革命、極具憲政特點的文官與內閣製度。這一刻,我覺得有必要對這個封建王朝進行重構。因為它表明,在那個傳統的農耕與儒家文化的王朝,已經產生了一些現代裂變的因子。
我對明史的真正關注與研究應該始於2008年。因為我的第一部長篇曆史小說《萬曆朝鮮戰爭》就動筆於那個時期。邊寫《萬曆朝鮮戰爭》的過程,其實也是對明史研究的過程。當時學術界對明史的研究比較碎片化,比如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專講萬曆怠政的原因,以及閑扯一些毫無關係的人與事,小野和子的《明季黨社考》則專講晚明的黨社運動,還有方誌遠、李洵、林延清、樊樹誌等學者的明史專著則專講一個皇帝,而杜車別那部《明朝滅亡原因和中國古代政治製度超前發展》著作,則專講晚明一些導致明朝覆滅的因素。市場上缺乏一部深刻、係統、全麵、顛覆性的重講明代通史的著作。所以,2010年6月份,我便開始了這部書稿的創作。但到了10月份,在寫了幾萬字後,頭腦中沒有一個清晰的架構。所以便停筆,又開始了學習與重構明史的過程。到了2011年7月份便推翻原來的書稿,重新進行創作。這次創作我一氣哈成、十分流暢的完成本書稿。2011年秋天和2012年春天我都沉浸在創作的愉悅之中。這種愉悅是任何事物都無法比擬的。它使我感到自己像一位洞悉曆史的巨人。也許以後我還會做其他事情,但此生做的最偉大的事情便是創作了這部明代通史的書稿。我相信時間會證明這點。
在創作的過程,我查閱了大量史料,其中杭州的一位女孩舊時漢月提供大量幫助。在此一並感謝。查閱史料的過程也是對明史觀梳理的過程。我又發現了一些有趣的事情。比如方誌遠認為成化王朝是整個明朝時代的轉折點,這種轉折是從思想、製度、經濟三方麵進行的;李洵認為正德的荒誕代表那個時代中國貴族的一種絕望。的確,皇帝是壓抑的,他們隻是作為一種執行禮儀的木偶存在。溥儀說,我隻是紫禁城的一個囚徒。除此之外,我還發現其他一些有趣的事情。比如嚴嵩,抗倭、開關、鹽稅改革都是在他主持下進行。嚴嵩就是一個替嘉靖背黑鍋的角色。他過的很苦,但就是因為迎合皇帝,被同僚打成奸臣。而張居正,這個曆史上偉大的官僚,整人的手段的確很陰毒,而且張的改革幾項都被實踐證明有問題。還有萬曆派宦官收礦稅,不是貪財,而是明代的財政的確到了山窮水盡的境地。天啟和崇禎最初都重用東林黨,但隨後發現這個黨派的確有問題,便又開始打擊。另外,王振、劉瑾、汪直、魏忠賢這四位在中國曆史上臭名昭著的宦官,其實都是極富改革意識的宦官。他們的聲名狼藉正是因為他們的改革觸動了官僚集團的利益。
最後,還有明朝滅亡的原因,跟曆史上其他封建王朝一樣,都是由於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裏,政府失去了調配資源的能力。
的確,在這個時代,在自己年輕時期,能完成這樣一部著作,我感到非常驕傲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