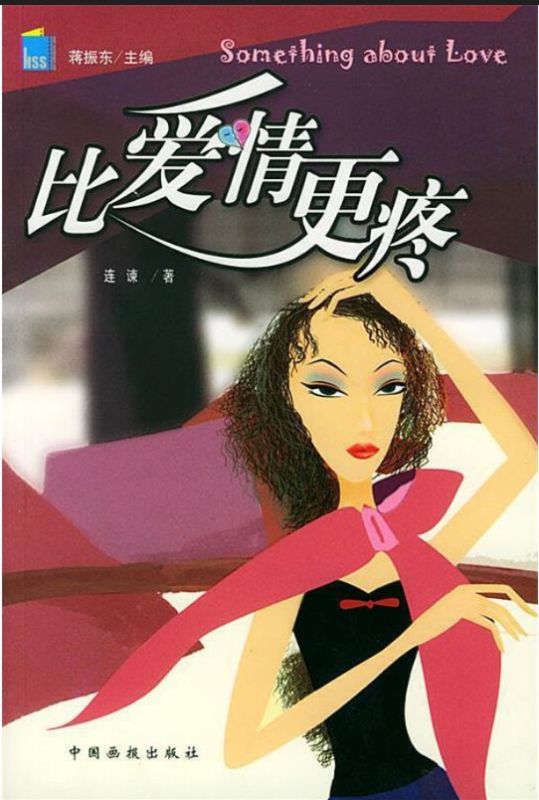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不是每朵玫瑰都為愛情盛開
文:連諫
(一)
櫻芝第一次打過電話,興奮衝撞著康陽的臉,扔下話筒,康陽說:“宴妮,你知道誰嗎?”
通話15分鐘,康陽至少喊了10次櫻芝櫻芝。
櫻芝是從新西蘭打過來的。在此之前,我不知道櫻芝。現在,從康陽的口氣以及神采,我知道櫻芝是個女孩,和康陽有著很多淵源。
那時,我和康陽正奮力經營著濟南文化路上的一間書店,以一平方厘米加一平方厘米的速度,賺一套盛裝未來的房子。
後來,櫻芝的電話密度是每晚一個,康陽放下電話後總在我臉上摸一下:“那個小黃毛丫頭。”
黯然的不安藏匿在我心底,不給康陽看見。
櫻芝是康陽的童年夥伴,距離是一牆之隔,翻過半人高的陽台,兩家人就可以不分彼此。那時,康陽和櫻芝趴在陽台上種太陽花,現在,據說太陽花已長滿康陽和櫻芝家的陽台,紛紛擾擾連在一起。
櫻芝14歲去新西蘭讀高中,走時帶著的一棵太陽花,如今已在她的新西蘭校舍陽台上一片燦爛。
康陽以及櫻芝的往事,在他們斷斷續續的聊天裏,是破碎細小的片段,被我用思維一點點重新串聯,如風幹的花朵,輕輕搖蕩在心裏,飄飄如蕩碎漣漪。康陽說:“那些陳年舊事她怎麼能夠記得。”我知道,康陽也記得,且保留著往日的鮮活。
我不說什麼,記得康陽說之所以留在濟南,是因為這裏有一個叫宴妮的女子,不然,這樣一座破敗的城市,如沒落地主,連沒落貴族都算不上,他怎麼會留下?
我像遊離在縫隙的魚,拚命引誘康陽講述和櫻芝的童年,關於櫻芝,如逐漸浮出水麵的花朵,一點點清晰:細軟微黃的頭發,貼在額上,耳邊常常插一朵若隱若現的粉色太陽花,臉上的茸茸感,陽光下,一片細微的金色閃爍。
康陽閉嘴時,我已經掉進想象:櫻芝,在新西蘭的櫻芝,像童話裏的美人魚。
而我,而我,像什麼?我沒命地尋找自己的可人之處,除了蘆柴棒,我找不到更形象的比喻。
我在夢裏流淚,康陽攬過我,我鑽進他的懷裏,哭泣無聲無息,懷著落岸之魚的驚恐。
我偷偷撥下電話線,康陽總是一邊吃飯一邊盯著話機,電話的靜默裏,他吃得寡然無味,丟下湯碗就擺弄電話,我的陰謀泄露,他不語,插上電話線,望著我笑,暖暖地說:“小女人。”
然後,我一口氣弄壞四部電話機。康陽買了十部話機,存在櫃子裏,我不再努力。隻說:“康陽,我愛你。”
康陽擁抱我:“小女人,櫻芝不過往事裏的影子而已,你何必介意。”
他試圖用一串愛你愛你愛你打消我的質疑,他不知道,我是多麼聰慧的女子,明白過分的強調其實是忘記的前提,人,隻有在即將丟掉或恐懼著丟掉時,才會想起諾言並努力承諾,外強中幹地鞭策自己堅持而已。
愛情走到這時,心已遊離。
我是個堅持必須看到結局的女子,即使我早已知道是最壞,即使我知道會被一下擊昏。
惶惑讓我瘦啊瘦的,在一陣子,所有的朋友問我:“不要命了?這麼瘦了還要減肥。”隻有康陽知道,我消瘦不停,是因為不快樂。
為了讓我快樂,打烊後,他拖著我穿梭在幹燥的濟南夏夜,指著一些我平素裏的喜歡說:“結婚時就買這個、那個。”其實,我們的內心一樣惶惑,隻是誰都不肯說。
我們總是什麼都沒買成,康陽買一朵玫瑰給我,我插在床頭上,夜晚,我們頭上有幽暗的花香在飄蕩,一朵比一朵暗淡下去。
(二)
床頭的玫瑰,插到了33朵。櫻芝就來了,她望著開門的康陽,眨著明晃晃的眼睛:“不抱抱嗎?”對我視若不見。
康陽望我。我笑,淚在心裏藏著。
櫻芝一下擁抱住他:“這是新西蘭禮儀。”我想說這是中國,卻說不出,我看櫻芝的眼睛,淡淡的琥珀色,依舊黃黃的頭發,散亂著溫柔的柔軟。
櫻芝鬆開康陽,轉身出去,拖進巨大的箱子,打開,一個玻璃尊,種滿了紛紛擾擾的太陽花,她擺在窗台上說:“從國內帶到新西蘭又帶回來。”
然後,她拖出一個盒子,裏麵是還在爬行的螃蟹。她進廚房,放進鍋裏:“想你在濟南肯定沒有新鮮的螃蟹吃。”
微藍的火苗,炙烤三個人的尷尬緘默。
櫻芝把它們放在盤子裏說:“吃吃。”招呼我們,如同主人。
康陽第一句話是:“櫻芝,你還是老樣子。”櫻芝嫣然一笑:“你也是嗎。”
她隻吃螃蟹腿,把豐腴的身子放在康陽麵前,說:“你們男人總會嫌吃腿太麻煩。”
康陽眼裏,一片波光瀲灩。
櫻芝邊吃蟹腿邊講她在新西蘭的故事,用了八年,她沒有拿到學士證書,熱衷於學習新西蘭飲食,學做各種各樣的新西蘭小點心。說到這裏,她陡然間抬頭:“康陽,我用八年時間學做點心給你吃。”
這是我早已預習過一萬遍的一幕,隻是沒想到來得這樣直接。我寧靜地盯住桌上的螃蟹,全是豐腴的身體,留給康陽。我的身體,蔓延上冰涼的溫度,在炎炎盛夏。康陽說:“櫻芝,怎麼不打招呼就來了?”
櫻芝忽然看著我:“你還沒介紹呢,這位是誰?”
康陽遲鈍一下:“我的女朋友,宴妮。”
我笑笑:“康陽說錯了,是朋友,不是女朋友。”
櫻芝就笑,太陽花一樣的靜謐暖色,洋溢在白皙的臉上:“我說呢,有女朋友怎麼不見你在電話裏提過。”
我說晚安。起身。康陽拉著我的手,第一次,他拉我時輕飄無力。
站在街上,康陽突然扳過我:“宴妮,我真的愛你。”我說:“相信,都八年沒見了,你們好好聊聊。”
一雙手,一個身體,在街上僵持。出租車來了,我揮手,康陽喊:“宴妮。”
我上車,司機問去哪兒,我說開。車子就走了,回頭望,康陽被黑暗緩緩吞噬。
車子開出一段,我說回去,車子回旋了一個不大的圈,回到與康陽分手的地方,是一片空蕩的夜,康陽已不見了。三年的愛情,我以為他會送我陪我一輩子,而現在,他隻送我從樓上到路邊,不足一百米的路程。一個路口丟失彼此。
望著空蕩蕩的路口,我的淚丟落在夜晚空寂的風裏。
回我的小房子,一棟七十年代老樓上有十個平米,是姥姥留給我的棲身之地。我和康陽在這裏開始戀愛,開始同居,隨著康陽畢業,他說這裏太擁擠,愛情沒有飛舞的空間會窒息。
我們租了離書店最近的一套二居室,有了寬闊的空間,愛情卻最終不是給我。
很久沒有回來了,連鑰匙都已生澀。進去就把自己埋進和心一樣寂寞的灰塵裏。
一個周,我陷在古老的沙發裏,等康陽來說:“宴妮,回去吧,櫻芝已經走了。”我是一個那麼不肯輕易死掉心的女子。所以,我沒有收拾滿屋子的灰塵。
(三)
第二個周,我收拾了屋子,康陽不會來了。
我邊流淚邊想康陽和櫻芝,有沒有摘下床頭那33朵逐漸幹枯的玫瑰?那是我的愛情,在櫻芝麵前,應以最快的速度枯萎。
夜晚的寂寥裏,還是忍不住的,電話就打過去,是櫻芝,我請她把床頭的玫瑰收起來,留給我。她告訴我早就摘下來扔掉了。我說哦。扣了。窒息了心的疼。
第三個周,我百無聊賴,看受潮而嘶嘶做響的電視,莫名地報了廣告裏正播著的廚藝學習班,往事傷感被鎖在屋子裏,連手機都關掉。
最後一門課程是西方麵點,其中有新西蘭小點心工藝,我一邊切碎水果一邊流淚,那麼簡單的工藝,櫻芝用八年去學,所有的盡善盡美,是她的愛。
兩個月後,我已是廚藝精湛的小女子,適合用來居家,學會的東西我想用來給一個男人做飯,比計劃未來,要實際得多,未來是看不見的,隻有現在,被抓在手裏。
回家,打開門,地上有從門縫塞進的紙條,散在暗紅的地板上,我一陣狂喜,想櫻芝已經走了,康陽來過。哪怕他有過錯,我亦願意承擔,因為愛他。
抓起來看,筆跡陌生,是康陽的朋友張卓,忽然地就不敢看內容,按時間順序排好,在地板上擺了很久,才張開眼。
張卓說:我來過一次,你不在。我又來過一次,你還不在……相同內容的五張紙。最後一張說:你的東西,康陽放在我家了,有時間給我電話,我送來。
它們被我攥成粘粘的碎片,被我用來擦淚,堅硬地劃疼皮膚。
(四)
東西堆積在張卓的沙發上,我坐在一側凝望它們,張卓給我一杯水。我說:“張卓,康陽幸福嗎?”
張卓緘默片刻:“康陽是誰?你幸福了就可以。”
我哭了,偎在堅硬的書茶杯或柔軟的衣服上,康陽連見我的勇氣都沒有,放棄得如此徹底。然後,張卓把肩膀借給我偎。
我走,張卓拎著我的東西,沉重如不堪的往事,走過一個垃圾箱時,我說:“張卓,丟進去吧。”
張卓看看我,我說:“丟進去。”張卓就掉進去,然後笑:“丟掉就好。”
是,不該的,能夠丟掉就好,能夠丟掉了不疼更好,可我做不到丟掉了不疼。
走了很遠,我折回去,一頭栽進垃圾箱,撿啊翻啊。“我想留一件紀念往事。”我這樣對張卓說,埋在垃圾箱裏的臉上全是淚。
我拎著一根紗巾走在街上。那年生日,康陽說濟南的冬天太冷,會凍壞我纖細的脖子,他就買了紗巾送我。濟南的冬天沒凍壞我的脖子,而康陽卻凍壞了我的心。
一晃三年過去,文化路上,我和康陽的書店變成冰吧,康陽不需要在這座如敗落地主莊園般的城市裏一平方厘米一平方厘米地賺錢買房子,他回了青島,那裏有海有他的家就有他的房子,不再需要努力。
(五)
我常去冰吧,要一杯冰蓮子粥,攪來攪去地慢慢想一些故事。三年裏,張卓是康陽丟在這個城市的友誼,我是他丟在這個城市的愛情,兩個人被放棄,不知什麼時候起,我和張卓被放棄在一起,用學來的廚藝為他燒菜,他吃得幸福,我做得平靜,很久很久一段日子,對於張卓我沒有愛情,向他索要孤寂的安慰而已。
我會不經意間就做了新西蘭點心,學了那麼多道西點,隻有新西蘭點心,是我的最拿手。張卓不吃,說討厭新西蘭點心。我知道,他隻是不想看見我往日的傷口,開在點心上。
這麼細心的愛護,我不可以不珍惜。
我以為三年的時間足以讓自己平靜,可櫻芝的電話來時,心卻依舊在陡然之間飛舞,她說:“宴妮,當年,康陽隻是想成全一個將死之人的願望,他最愛是你,誰忍心拒絕一個愛了他十幾年而將要死去的女孩的願望呢?原諒他的善良還有我的自私,我要死了。”
她收線,我已傻,對站在身後的張卓,視若不見,恍然之間,我想:其實,這麼多年來,自己一直在等一份解釋,成全自己脆弱的自尊。
我去,櫻芝已在彌留之際,康陽瘦如幹枯麥管,脆弱而單薄。櫻芝是淋巴癌,痛疼折磨得她已不像樣子,她躺在病床上,望著我笑了一下,就過去了,安詳如嬰孩,柔軟的黃發已經褪盡,浮腫的臉上一片蒼涼的留戀。
安葬好櫻芝的中午,我和康陽,站在街上,他眼裏除了疲憊還是疲憊,當年的康陽全然皆無。
康陽眼裏瀉落不止的疼,是因為櫻芝。我說:“康陽,什麼時候發現的櫻芝的病情?”
他望著天空告訴我,半年前,櫻芝開始莫名地虛弱,莫名地疼,常常疼得捏碎製作中的新西蘭小點心。
我知道了櫻芝的謊言,不過是想把最愛的人交付給可以信賴的女子,在她眼裏,我便是的,不是施舍,不是憐憫,還是因為了愛。我寧願康陽說在三年前,櫻芝出現時就發現了病情。我寧願相信櫻芝的謊言,康陽卻揭穿了。
康陽牽著我,不是愛,是疲憊,他需要一個懷抱一個安慰。
晚上,我們坐在陽台上,望著滿天的星鬥沒有話說,望到天空發白,康陽依在我肩上睡著,入睡的臉,脆弱如嬰。清晨,我搖醒他:“康陽,一切都過去了。”我第一次看見了康陽的淚,是給櫻芝的眷戀。
康陽看著我走下樓梯,眼睛一片茫然。
回濟南已是夜裏,張卓躺在床上,一片潦倒,說:“宴妮,回來了?”他遲遲疑疑地望著我,想抱又不知從何下手。
我笑笑:“回來給你做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