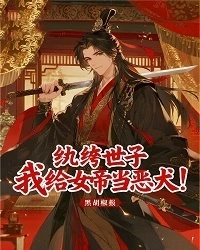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4章
“大人!”
一道殘影閃過,北鎮撫司千戶趙恪瞳孔驟縮,下意識地一個箭步衝上前,在徐恪的臉與地麵親密接觸前,一把將他撈了起來。
入手滾燙的溫度讓趙恪心中一凜。
這個剛剛還用神鬼莫測的手段鎮住全場、談笑間便將一樁死案盤活的少年,原來隻是一具隨時可能碎裂的琉璃。
“快!傳大夫!”趙恪抱著懷中輕飄飄的身體,對著周圍目瞪口呆的緹騎們發出一聲怒吼。
懸鏡司內,亂成了一團。
徐恪被緊急安置到了內院一間還算幹淨的廂房。
大夫來了又走,留下一堆苦澀的湯藥和一句“憂思過甚,寒氣攻心,性命暫且無虞,但高燒難退,切不可再勞心費神”的囑咐。
趙恪站在床邊,看著躺在榻上雙目緊閉、眉頭緊鎖的徐恪,眼神複雜到了極點。
他一方麵為那神乎其技的查案手段所震撼,另一方麵又為徐恪這破敗的身體感到憂慮。
三天之期,如今連主心骨都倒了,這案子還怎麼查下去?
最關鍵的是,他已經被徐恪用“一成賞錢”的陽謀,死死地綁在了這條船上。
船要是沉了,他趙恪也得跟著喝水。
就在趙恪心煩意亂之際,一名緹騎神色慌張地從外麵衝了進來。
“千戶大人!不好了!都察院的人......闖進來了!”
趙恪臉色一變:“都察院?他們來幹什麼!”
“是左都禦史李世蕃!他......他帶著人,指名道姓要我們交出徐大人,說、說是懸鏡司以罪臣掌印,穢亂國法!”
“放他娘的屁!”趙恪勃然大怒,腰間的繡春刀“嗆啷”一聲出鞘半寸,“兄弟們,跟我出去!我倒要看看,誰敢在懸鏡司的地盤上撒野!”
然而,當趙恪帶著一眾殺氣騰騰的緹騎衝到指揮大廳時,那股滔天的氣焰卻不由自主地弱了下去。
大廳中央,站著一位須發皆白、身著緋色官袍的老者。
他手持象牙笏板,麵沉如水,眼神清正,不怒自威。
正是當朝左都禦史,被譽為“文官風骨”、“朝堂啄木鳥”的李世蕃。
他身後跟著幾名年輕禦史,個個昂首挺胸,一臉正氣。
“趙恪,你好大的膽子!”李世蕃看到緹騎們拔刀,不退反進,厲聲喝道,“懸鏡司乃天子親軍,監察百官,何時成了藏汙納垢、包庇罪囚的匪窩了?”
趙恪握著刀柄的手青筋暴起,卻遲遲不敢下令。
打,他不敢。
李世蕃代表的不是個人,是都察院,是朝廷的法理,是文官集團恪守了數百年的“祖宗之法”。
他今天敢動李世蕃一根汗毛,明天全天下的讀書人就能用唾沫星子把他淹死,無數的彈劾奏章能把女帝的龍案都給埋了。
這是懸鏡司最薄弱的一環,他們是皇帝的刀,卻不是朝廷的法。
“李禦史,徐大人乃是奉陛下口諭查案,何來罪囚一說?”趙恪咬著牙,沉聲辯解。
“荒唐!”李世蕃用笏板重重一頓地,聲震屋瓦,“徐恪乃安國公府餘孽,罪證確鑿,聖旨已下,明日便要明正典刑!陛下或有愛才之心,一時被奸佞蒙蔽,我等身為言官,豈能坐視國法淪為兒戲?立刻交出罪囚徐恪,停止對周侍郎的無端構陷,否則,老夫今日便一頭撞死在這懸鏡司的門前,也要維護大周的體統!”
一番話說得是擲地有聲,大義凜然。
趙恪被逼得節節敗退,額角滲出了冷汗。
他知道,這老頭子是真的幹得出來。
這根本不是來問罪的,這是文官集團對女帝的一次正麵政治衝鋒!
進退兩難之際,趙恪一咬牙,轉身對手下低聲道:“守住這裏,任何人不得妄動!”
說完,他快步衝向內院。
“吱呀”一聲,廂房的門被猛地推開。
“大人!您醒了!”趙恪看到床上的人影動了一下,又驚又喜。
徐恪剛剛轉醒,頭痛欲裂,渾身發燙,連坐起來的力氣都沒有。他看著焦急的趙恪,聲音微弱得像蚊子哼:“外麵......怎麼了?”
趙恪用最快的速度將外麵的情況說了一遍。
所有緹騎都覺得這次死定了,女帝也保不住他們。
徐恪聽完,卻沒有絲毫慌亂,反而低聲咳嗽起來。
咳得撕心裂肺,仿佛要把肺都咳出來。
在趙恪焦灼的目光中,他終於緩過氣來,用隻有兩人能聽見的聲音,下達了三條匪夷所思的命令。
“第一,去,請李禦史到正廳稍坐,上最好的茶。告訴他,我重病在身,正在更衣,馬上就到。”
趙恪一愣:“大人,這是示弱......”
“第二,”徐恪打斷他,“把我那塊陛下給的令牌,用一個最顯眼的托盤盛著,放到我床頭的桌案上。”
“第三,”徐恪的眼中閃過一絲狡黠的微光,“待會兒無論我說什麼,你都不要出聲。但記住,你要表現得比我還憤怒,越憤怒越好。”
李世蕃在正廳等得心頭火起,一杯茶都見了底,也沒見到那個“罪囚”的影子。
“豎子無禮!”他重重放下茶杯,再也按捺不住,帶著人便直闖內院。
他已經想好了,見到那個黃口小兒,便要先聲奪人,以雷霆之勢將其拿下,徹底打掉懸鏡司的囂張氣焰。
然而,當他怒氣衝衝地推開病房門時,卻愣住了。
預想中權臣作威作福的場麵根本沒有。
隻見一個麵色慘白如紙的少年,正裹著厚厚的被子,虛弱地靠在床頭,劇烈地咳嗽著,仿佛隨時都會斷氣。
整個房間裏,最醒目的,反而是床頭桌案上那個紫檀木托盤,以及盤中那塊象征著女帝親臨的玄鐵令牌。
沒等李世蕃發難,徐恪已經搶先開了口,聲音虛弱,卻字字清晰。
“下官......咳咳......不知李禦史大駕光臨,有失遠迎。您是來......協助下官,為陛下分憂的嗎?”
一句話,直接給李世蕃整不會了。
他滿肚子“國法”、“體統”的宏大敘事,被對方輕飄飄一句“協助辦案”給堵了回去。
這一下,仿佛掄圓了拳頭,卻打在了一團棉花上,有力無處使。
他把衝突的性質,從“私人問罪”,強行拉高到了“為陛下辦事”的公共層麵。
“一派胡言!”李世蕃臉色一沉,正要發作。
徐恪卻像是沒看見他的怒火,掙紮著抬起手,指向床頭的令牌,臉上擠出一個比哭還難看的“真誠”笑容。
“李禦史,您來得正好!此案千頭萬緒,下官又......咳......又身染重病,實在是有心無力,恐有負陛下三天之期啊!”
他喘了口氣,用一種托付後事的語氣說道:“既然您來了,想必也是心憂國事。這勘察百官之權,就請您代為執掌!這令牌在此,您拿去!周文淵的案子,就全權拜托您了!”
說著,他竟真的做出了一個“請”的手勢,仿佛在托付什麼無上榮耀。
李世蕃瞬間僵在了原地,如遭雷擊。
他身後的幾個年輕禦史,也全都傻了眼。
接?
接了這塊令牌,就等於接下了女帝那道“三天之內,要看到人頭”的死命令!
他李世蕃是言官,不是酷吏,查案?
他拿什麼查?
辦成了,他落下一個“諂媚君上,構陷同僚”的罵名,一輩子清譽毀於一旦。
辦砸了,那更是欺君之罪,女帝正好借此機會,把他這個眼中釘連根拔起!
不接?
徐恪見他不動,立刻露出一副痛心疾首的表情,猛地轉向身旁的趙恪,聲音陡然拔高了幾分。
“趙千戶!你聽見了嗎?”
趙恪心領神會,瞬間戲精附體,一張臉漲得通紅,手死死按住刀柄,咬牙切齒地瞪著李世蕃,憤怒的表情仿佛在說“你他媽居然敢不接”。
徐恪繼續唱著雙簧,捶著床榻,悲憤道:“我本想請李禦史為國分憂,他......他竟不願為陛下分擔!唉!看來,這為陛下盡忠,拋頭顱灑熱血的臟活累活,隻能我們懸鏡司自己拚命了!”
這套組合拳下來,李世蕃的臉已經從鐵青變成了煞白。
他被死死地架在了火上。
接,是萬丈深淵。
不接,就是“不忠”,就是當著懸鏡司所有人的麵,承認自己不敢為女帝分憂。
這個口實要是落下了,明天徐恪就能反參他一本!
他一個清流言官,一生最看重的就是“忠君”二字,這簡直比殺了他還難受!
他看著病榻上那個氣息奄奄、仿佛下一秒就要咽氣的少年,後背卻竄起一股徹骨的寒意。
這哪裏是個少年,這分明是個披著人皮的怪物!
不跟你講道理,不跟你辯法理,他直接挖了一個人性和忠誠的陷阱,笑眯眯地看著你往下跳。
“你......你......”李世蕃指著徐恪,氣得渾身發抖,最終卻隻能從牙縫裏擠出四個字。
“豎子!奸猾!”
說罷,他猛地一甩袖子,轉身便走,步履竟有幾分踉蹌,仿佛打了場敗仗。
一場足以顛覆整個任務的風波,就這麼被徐恪在病榻上,用幾句話消弭於無形。
做完這一切,徐恪再也支撐不住,眼前一黑,整個人向後倒去,冷汗瞬間浸透了被褥。
病情,雪上加霜。
趙恪連忙上前扶住他,看向他的眼神,已經從最初的敬畏,變成了一種近乎恐懼的崇拜。
就在此時,一名緹騎信使跌跌撞撞地衝進院子,臉上混雜著塵土與焦急,他單膝跪地,聲音嘶啞地喊道:
“大人!江南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