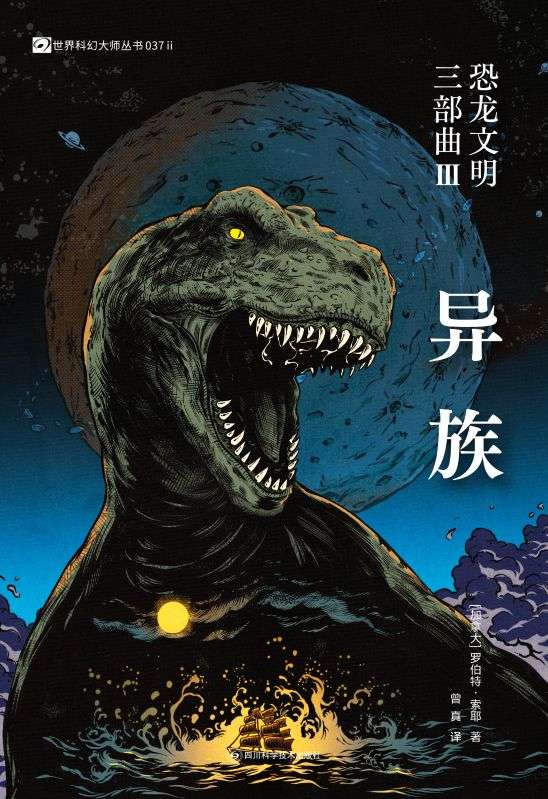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五章
娜烏-默克蕾博的病曆本
很明顯,關於交談治療的消息已不脛而走。我接到國王的旨意去治療一個新的病人。之前,我一直希望這個病人就是國王他自己。我想,兩千日前對他領導地位發起的挑戰可能引發了他的情緒問題。沒錯,他在抗擊黑死獸的過程中表現出色,但那場挑戰如果至今仍讓他心有餘悸,也不足為奇。畢竟他目睹了六名省長學徒的死亡,而且,似乎這還不夠慘烈,之後他還被迫硬生生地將自己的雙臂咬了下來。
但見了以後才知道,我的病人在政府中的職位還沒那麼高。可無論如何,薩爾—阿夫塞也可以算是一個有趣的病例了。我已經大致看過了與他相關的信息。阿夫塞正值中年,大概三十四千日前在阿傑圖勒爾省的卡羅部族被孵化出來。他智商極高,十三歲時就被征召到首都,成了皇家占星大師塔科-薩理德眾多學徒中的最後一名學徒。
阿夫塞的一生自然過得很精彩。當戴西克爾號帆船進行首次環球旅行時,他在船上;是他闡明了“上帝之臉”的真實情況,並發現我們的星球將最終碎裂成一道環帶。一開始,他的觀點被宣布為異端,而已經謝世的、當時的首席祭司德特-耶納爾博用一柄慶典上用的匕首將他的眼珠剜了出來以示懲戒。但魯巴爾獵手的地下組織卻宣稱阿夫塞就是那個家夥——魯巴爾臨終時所預言的最偉大的雄性獵手。阿夫塞的狩獵——當然,是在他失明前——確實很壯觀:他殺死了有史以來最龐大的雷獸,打敗了一條巨大的大水蛇,還放倒了一隻尖齒顎。
阿夫塞同瓦博-娜娃托的八個孩子因他的功績而得到了赦免。同魯巴爾獵手緊密聯盟的血祭司們都拒絕吞噬他的任何一個孩子。
現在,這位出色的人物開始做噩夢了。
我一直懷疑天才與瘋子隻有一線之隔。好了,我很快就能知道,將我們推向星係的人到底是受到了些許困擾,還是如同他的詆毀者所說的那樣,完全是個瘋子……
石柱區已失去了它原有的吸引力。哦,到首都來遊玩的人們還是會跋涉到這裏來,觀看臨海的山崖邊高高的草叢中由四十九塊巨石排成的石陣。沒有人知道這些巨石是什麼時候形成的,但肯定是在遙遠的史前。
可是,與托雷卡在弗拉圖勒爾省挖掘出的古代宇宙飛船相比,石柱區就沒那麼重要了。那艘龐大的飛船已存在上百萬千日了。即使是作為昆特格利歐恐龍最古老的居住地的石柱區,也無法與之相提並論。
無論如何,阿夫塞仍堅持常去那裏走走,並將那裏作為給自己學徒上課的露天教室,當他一個人的時候,則在那裏獨自沉思休憩。
當然,他獨自一人的時間很少。他的蜥蜴高克時常跟他在一起,躺在它最喜歡的石柱區的大石頭上曬太陽。阿夫塞也有一塊自己喜歡的石頭。此刻,他正坐在這塊石頭上,尾巴垂在身後,失明的雙眼朝向岩石遙遠的邊緣。他能聽見翼指在空中飛起降落時發出的“啾啾”聲,以及草叢中蟋蟀和其他昆蟲的鳴叫。雖然他坐在首都港口往北較遠的地方,卻仍能聽見船隻鳴響鐘鼓的聲音和商人們偶爾為新到的貨物討價還價的聲音。海邊的氣味也很重,風中帶著鹹鹹的味道,夾雜著馥鬱的花香。
“能允許我進入您的地盤嗎?”阿夫塞沒有分辨出說話人的聲音。
他轉向話音傳來的方向。“哈哈特丹,”他說,“您是哪位?”
聲音更靠近了,但風轉向了,阿夫塞聞不到激素的味道,因此也辨別不出來人的性別。
“我叫娜烏-默克蕾博,”根據說話人的音量來看,兩人的距離應該在十五步以內,“剛從瑪爾圖勒爾省的魯朵部族遷過來。”
阿夫塞沒必要再做自我介紹了。首都的盲人本來就不多,而他的飾帶半黑半綠,是出逃項目的顏色,將他同其他盲人區別開來,即使不知道他經常到石柱區的人也不會混淆。但他還是謙虛地做了自我介紹,然後鞠了一躬,說:“很高興你能來,娜烏-默克蕾博。迪博說過他會請你來見我的。”迪博之前提到默克蕾博時用的是“她”,但她仍站在阿夫塞的下風處,阿夫塞沒法親自證實這一點。
“我很高興能為你效勞。”默克蕾博說。過了一會兒,她又說:“我聽說,嗯,你睡得不太好。”
阿夫塞點點頭。
“今天達爾-蒙達爾克還捎話給我,說你的眼睛已經再生了,但你還沒有複明。”
“那也是真的。”阿夫塞沉默了一下,“你能幫幫我嗎?”
“不能,”默克蕾博毫不遲疑地回答道,“我幫不了你。”她抬起手示意阿夫塞先不要反對,隨後磕了磕牙,意識到阿夫塞根本看不見她的手勢,“但請別誤會,交談治療確實能幫你,但我什麼忙都幫不上。問題在你自己身上,治療也得靠你自己。我隻能控製治療的過程。”
阿夫塞皺了皺鼻口,說:“我聽不懂。”
“你對心理學知道多少?”
“我知道那是對人的意識的研究。”阿夫塞說,“古代心理學家多爾加是公認的鼻祖。”
“沒錯。”默克蕾博說,“但多爾加算不上心理學的奠基人。她認為,頭部和尾部分別是我們性格中相抵觸的兩種力量存積的地方——藝術感知力和感官存在於腦部,而無意識和無知覺的力量則存在於尾部。”
“是的,我還記得這一點。”阿夫塞說。
“當然,這個觀點已經過時了。嗯,我們的性格中確實存在兩種相對的力量——意識和潛意識——但二者均存在於我們的腦部,而不是肢體的各個部位。意識包括明確的、知曉的和後天學習獲得的東西——也就是我們能意識到的東西。潛意識則由本能和基本衝動、動機構成,是我們意識不到的領域。意識和潛意識的爭鬥就構成了我們的性格。”
“但意識就是我們真正的自我啊。”阿夫塞說。
“不是。意識可能代表了我們希望成為的樣子,或者宗教教義宣揚的人格,但潛意識的作用與意識同等重要,它也在引導著我們的行為。”
“可如果潛意識是不可知的,那不就等於不存在了嗎?”阿夫塞回答道,“與多爾加同時代的克拉德克說過,不存在的物質不能算物質。換言之,沒有物質實體承載的概念是毫無意義的。”
“噢,一點兒沒錯。”默克蕾博說,“也許我的闡述不夠準確。潛意識在通常情況下是不可知的,但我們可以一同去探求它,就像望遠器能讓你看到肉眼看不見、從前也一無所知的天體運行一樣。好了,薩爾-阿夫塞,如果你願意去探求你性格中一直受壓製而隱藏的未知部分,我們將有可能找到你做噩夢的根源。”
飛船看起來像是在熔化。
外星飛船仍從岩壁突出來,但飛船正下方的岩石已經變成了同飛船一樣的藍色,就好像熔化的液體在順著峭壁流淌下來。可飛船並沒有熔化——它棱角分明的船殼仍完好無損,岩壁上的藍色物質卻還在蔓延。
娜娃托如一隻綠色的蜘蛛般,沿著峭壁上用金屬螺絲固定住的攀爬繩往下爬。她還在岩層上,但大約十五步以下的繩梯正好同流動的藍色物質持平。她繼續往下爬,尾巴垂在身後,一直爬到藍色物質觸及不到的地方。
粗糙的繩梯通常會在風中微微擺動,但如今卻像被粘在了岩壁上的藍色覆蓋物上麵。娜娃托爬到了藍色物質的底線上停住,岩壁再度暴露在外。她將指尖劃過岩石與藍色物質交界的地方。她一直以為藍色物質就像樹幹上流過的汁液一樣,並沒有與岩壁牢牢附著在一起,但如今看上去,藍色物質倒像是滲進了岩石。這也有道理:藍色物質剛才是液態,如今風幹板結了。它很可能流進了砂岩的縫隙。
但是,如果藍色物質凝結前是液態——用熔融的蠟作類比還算恰當——那它如今已經完全凝固了。可它一點兒黏性都沒有,不可能曾經是固態以外的其他形態。
這東西一定是從飛船裏流出來的,因此隻可能覆蓋在岩石表麵。除了移動到外界的橘黃色粉末外,飛船沒有外泄過任何物質,而即使覆蓋岩壁的藍色物質隻有蛋殼那麼薄,那也已經比所有的粉末還多了。
娜娃托又往下爬了一段,在繩梯被藍色物質粘連住的那一段路程,她攀爬起來很困難。此刻,她的雙眼正好同一顆固定繩梯的螺絲一樣高,這顆螺絲周圍已經全是藍色物質了。這就是證據,她想,這就證明了藍色物質最初是液態的,它從螺絲周圍流過,而除了螺絲頭以外,這顆螺絲的其餘部分都深埋在岩石中。
在螺絲的洞裏應該很容易看見藍色覆蓋層到底有多厚。娜娃托隨身帶著工具袋,就在她的尾巴上。她用榔頭的“八”字嘴鉗住螺絲頭,彎曲雙腿,用腳抵住垂直的岩壁,利用膝蓋伸展的力量將螺絲拔出來。
她使了幾次勁,然後螺絲猛地被連根拔起,娜娃托像攀岩的人一樣在岩壁上飛蕩開。她鬆開榔頭和螺絲,任由它們墜落到山下的海灘上。失去了螺絲的固定,攀爬繩從岩壁脫開了。娜娃托死命抓住繩子,同它一起在空中旋轉。最終,她重新掌握了平衡,蕩到螺絲洞邊。要看清洞裏的情形很難;每當她把臉湊近時,頭部的陰影就把螺絲洞擋住。但她還是努力看到了。
螺絲洞裏全是藍色。
要說螺絲洞太鬆了,以至於藍色液體一路流進了洞中並凝固下來,這個可能性極小,但突然間,娜娃托明白過來事情根本並非如此。她大可以稍後挖掘藍色物質同砂岩交界的地方來證實這一點,但即使是現在,她也已經明白了。
藍色物質不是覆蓋層,不是從宇宙飛船中流出來並凝固的液體。
不,岩壁本身已經變藍了。不知怎麼的,整個岩壁正慢慢變成同古老的飛船一樣無比堅硬的物質。
等到托雷卡和巴布諾返回戴西特爾號後,克尼爾和斯拜爾頓帶回來的異族恐龍的屍體已經擺放在托雷卡的解剖桌上了。在各種各樣的地質勘探過程中,托雷卡已經收集了很多生物標本。他就常常在這個由船艙改建的實驗室裏解剖動物。南極類似翼指的潛水者也是在這裏解剖的,就是這種會遊泳的生物首次給他帶來了提出進化論的靈感。
房間的中央是一張解剖桌,桌麵由兩塊寬木板構成,分別從兩側向中央微微傾斜。但木板正中央並沒有完全合攏,而是留下了一條細小的縫隙,好讓血液流到下麵的陶罐裏。
托雷卡原本打算讓每個人都看看這具屍體,這很有可能是他們近距離觀察異族恐龍的唯一機會。然而,觀察者們的激烈反應卻讓他驚詫不已。從實驗室裏走出來的人們都探著爪子,而有一個人——老比爾托格,戴西特爾號上資曆最深的大副——走出來時的步伐甚至有些躍動的姿勢。雖然沒來得及看的船員們提出了抗議,托雷卡卻堅持不再讓人進入實驗室。任何能激起一丁點兒地盤本能的舉動都必須明令禁止。托雷卡常常想起蓋拉多雷特號的故事,那艘時運不佳的帆船被海風吹到了岸邊,甲板上七零八落地躺著船員們早已腐敗的屍體,有些甚至還保留著垂死掙紮的跡象。
夜已深了,但今晚是偶數夜,托雷卡與一半船員都會保持清醒,剩下的一半船員則已進入夢鄉——這樣輪班當值是為了避免激起地盤爭鬥本能——他決定點起燈開始解剖。
異族恐龍的肩胛骨和一部分脊椎已經被克尼爾撕咬開了,托雷卡拿起一把解剖刀,但在動手前卻有些遲疑。此前他解剖過的動物成百上千,而且也早已研究過昆特格利歐恐龍的解剖圖,但他從未切割過任何人的肢體。盡管異族恐龍的皮膚是黃色而不是綠色,但那很顯然是一隻恐龍;他身上佩戴的銅飾反射著跳躍的燈火。
當昆特格利歐恐龍死亡的時候,人們會為他舉行一係列儀式,包括在禮拜堂為其禱告,讓親人悼念五天,最後再將遺體埋葬在預先劃定的墓穴中,讓他回歸自然。
但這隻異族恐龍卻無法按照他自己的習俗入土為安。實際上,因為托雷卡一行人很快就不著痕跡地逃走了,遇難恐龍的同胞們在短期內甚至不會察覺到他的死亡,隻有在最後尋覓未果的情況下才能下此定論。
托雷卡覺得隻把這具屍體當作標本是不對的。他放下解剖刀,回了自己的房間一趟,很快拿來了魯巴爾獵手祝禱書,找到一段合適的禱文,輕聲對著遺體念道:
“我對這位不知姓名的死者表示哀悼,因為同他成為摯友的機會已經錯過。盡管我們不曾相識於塵世,但也許會在天堂裏偶遇,在那裏並肩狩獵。你去往天堂的旅程將是安全的,陌生的朋友,因為我們都是上帝之手創造的靈魂。”
念完後,托雷卡沉默了一陣,然後拿起解剖刀開始工作。
異族恐龍的骨骼結構跟昆特格利歐恐龍十分相似。他的手臂同肩膀的連接方式與昆特格利歐恐龍並無二致,脊椎固定背部上層肌肉的序列也很相似。
托雷卡將屍體翻過來,切進他的胸膛。多數肉食性爬行動物都有兩種肋骨:從脊椎延伸出來的大肋骨和通過肌腱同背部肋骨相連的胸部小肋骨。異族恐龍也有這樣的小肋骨,實際上,托雷卡將手壓在他的皮膚上數了數,發現異族恐龍的脊椎、背部肋骨和胸部肋骨的數目也同昆特格利歐恐龍一致。
在查看下半截屍身前,托雷卡先看了看他的頭顱。這裏的結構有些不同。異族恐龍的頸部肌肉不及昆特格利歐恐龍結實,這是講得通的,因為前者的下頜不太突出,使得頸部需要支持的重量較輕。前者眼球中有一塊鞏膜骨,這倒更像黑死獸和其他一些草食類爬行動物,但昆特格利歐恐龍沒有這一構造。此外,異族恐龍的鼻子上有幾個小角和骨狀瘤,使得他的頭部看起來更像黑死獸,而不像昆特格利歐恐龍的頭那麼光滑流暢。
托雷卡重新擺放了一下屍體,以方便解剖下腹。小肋骨原本會給簡單的腹部解剖製造困難,但是,同昆特格利歐恐龍一樣,異族恐龍前後兩組肋骨之間有一道縫隙,中間隻有皮膚、肌肉和肌腱覆蓋連接著。托雷卡在那裏劃了一條垂直的長口子,然後再水平劃了很深的一道。他將劃開的四片皮膚翻開,露出腹腔。
裏麵有些硬硬的藍綠色東西。
一塊砂石?食肉動物怎麼會吞砂石!而且砂石也不可能有這麼大!
隨後他意識到了那是什麼。從形狀和大小上看,這跟昆特格利歐恐龍的也差不多,隻是那怪異的顏色讓托雷卡沒有立刻辨認出來。
那是一枚蛋。
一枚還沒見天、未及孵化的蛋。
但這隻異族恐龍看起來像是雄性,因為他長著垂肉袋。難道他把蛋吃下去了?
托雷卡將屍體傾斜,查看生殖器上的褶層。毫無疑問——這是一頭雌性。或許兩種性別的異族恐龍都有垂肉袋。真是奇妙。
他輕輕將屍體放平,將手伸進洞開的腹腔。他的雙手沾滿了黏滑的體液,生怕將蛋滑落到地上,因此加倍小心地將它捧了出來。蛋的中軸線隻比托雷卡的手掌略長幾分。
腹腔內還有一枚蛋。
托雷卡輕輕地將蛋放到地上,以免晃動的船身讓蛋從解剖桌上滾下來,然後將第二枚蛋也取了出來。
後麵還有一枚蛋,他也給取了出來。之後看見的就是第四枚蛋的碎片,以及塗滿蛋黃的腹腔壁:這枚蛋在體內就被壓碎了,或許是克尼爾將異族恐龍摔倒在地的時候碎的。
此外便沒有別的蛋了。
昆特格利歐恐龍通常一次生八枚蛋。如果這隻恐龍不是特例的話,她的種族一定是每次生四枚蛋。
完好的三枚蛋都已長成,有堅硬光滑的蛋殼,似乎就快要生出來了。事實上,托雷卡覺得,或許他們遇見的這隻異族恐龍是在沙灘上尋覓合適的生蛋地點。若真是如此,那這些蛋也許還有救。他聽說過從臨死的母體身上把蛋取出來的事情。
托雷卡急匆匆跑去找包裹蛋的皮革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