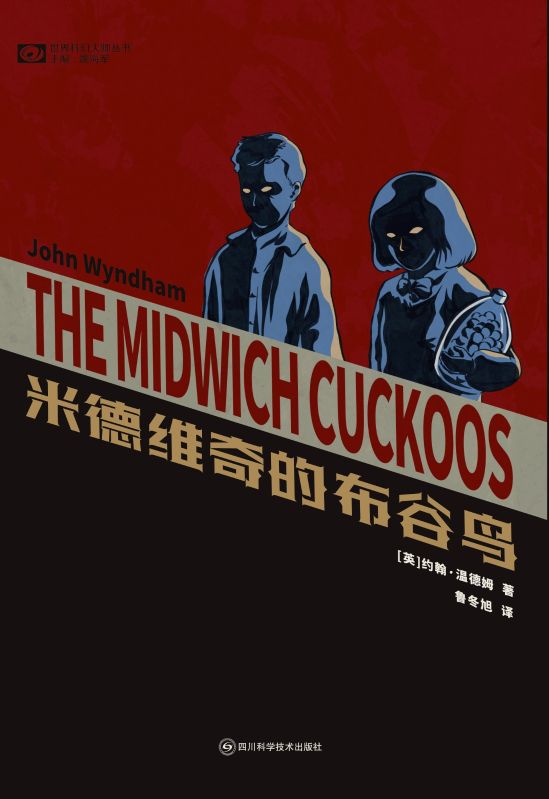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四章 米德維奇行動
大約就在我和珍妮特接近特雷恩的時候,艾倫·休斯少尉正與消防隊長諾裏斯並肩站在奧普雷路上,看一名消防員伸出長長的消防鉤去鉤倒下的救護員。現在,鉤子鉤住了傷員,開始把他朝這邊拖。傷員的身體在柏油路上被拖行了一米多——然後他突然坐起身,咒罵起來。
艾倫覺得自己從未聽過這麼“優美”的語言。到達現場時的嚴重焦慮已經緩解,因為他發現不管受害者們遭遇了什麼,盡管他們十分安靜地躺在地上,卻實打實地在呼吸著。現在可以確定,傷員中至少有一人雖然中招足有九十分鐘,但並無明顯不良反應。
“很好,”艾倫說,“如果他沒事,那麼看起來其他人可能也不會有事——但這並不能幫我們判斷那玩意兒是什麼。”
下一個被鉤子鉤住拖出現場的是郵差。他躺在那裏的時間比救護員長一些,但同樣非常令人滿意地自然蘇醒了。
“讓人暈倒的界限似乎非常清晰——而且是靜止的。”艾倫又說,“有誰聽說過完全靜止不動的毒氣——何況這裏還吹著微風?這說不通。”
“也不可能是地麵上的什麼液體的揮發物。”消防隊長說,“他們就像被錘子砸中似的突然倒下去了,我從來沒聽說過有這樣的東西,你聽說過嗎?”
艾倫搖了搖頭。“而且,”他讚同地說,“任何高揮發性的東西到這會兒肯定已經散了。再說,也不可能昨天晚上揮發,讓公共汽車還有其他車中招。這輛公共汽車應該是十點二十五分到米德維奇的——那之前幾分鐘我還親自開過這段路。當時沒有任何異常。事實上,這一定就是我快要進奧普雷時遇到的那輛公共汽車。”
“不知道影響範圍有多遠,”消防隊長若有所思地說,“肯定波及挺廣的,不然我們會看到試圖往這邊來的東西。”
兩人繼續迷惑不解地凝望著米德維奇方向。在事故車輛的後方,道路繼續延伸,路麵看上去暢通無阻,全然無辜地微微閃光,通向下一個轉彎處,和任何一條雨後快要幹透的道路毫無二致。現在,晨霧已經散去,能看見米德維奇教堂的塔樓從樹籬裏伸出來。如果不看眼前的景象,那遠處平凡的風景簡直是神秘的反義詞。
在艾倫手下兵士的協助下,救護員繼續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把傷員鉤拽出現場。受害者似乎都對之前發生了什麼毫無印象。每個人醒過來後都機敏地坐起身,堅決主張旁人也能看清的明顯事實:他們不需要救護人員的幫助。
下一項任務是把完全翻倒的拖拉機清走,這樣才能開始清理前麵的車輛及其中的人員。
艾倫把指揮工作交給中士和消防隊長,自己翻過田邊的梯磴。梯磴另一邊的田間小路通向一個小土包,站在上麵能更清楚地看見米德維奇。他看見若幹建築的屋頂,包括凱爾莊園和格蘭奇研究所的,還看見修道院廢墟上最頂部的石頭,以及兩股灰煙。平淡無奇的場景。但再往前走幾米後,他看見四隻羊一動不動地躺在田裏。這景象讓他不安,雖然他現在知道羊沒受什麼實際損害,但這說明屏障地區比他希望的更廣。他仔細觀察那四隻羊和更遠處的風景,發現再遠些的地方還有兩隻側躺著的牛。他靜靜地看了一兩分鐘,確認牛沒有任何動作,便轉身若有所思地走回路邊。
“德克爾中士。”他喚道。
中士走過來行了軍禮。
“中士,”艾倫說,“我想請你去弄一隻金絲雀——當然是關在籠子裏的。”
中士眨了眨眼。
“呃,長官。一隻金絲雀?”他不自在地問道。
“嗯,我想虎皮鸚鵡也行。奧普雷肯定能找到。你最好開吉普車去。跟鳥的主人說,如果需要補償,我們會支付的。”
“我——呃——”
“趕快行動,中士。我要你盡快把鳥弄來,越快越好。”
“好的,長官。呃——你要一隻金絲雀。”中士又重複了一遍,以確認自己沒聽錯。
“是的。”艾倫說。
我意識到自己正臉朝下在地麵上滑動,非常奇怪。上一刻我還在飛奔向珍妮特,下一刻,中間沒有任何空當的,我現在……
滑動停止了。我坐起身來,發現自己被一群人圍著。其中一個是消防員,正把一個看起來能殺人的鉤子從我的衣服上解下來。一個聖約翰醫院的急救員用一種專業的、充滿希望的目光望著我。一個非常年輕的二等兵提著一桶白石灰漿,另一個二等兵拿著一份地圖,一個同樣年輕的下士拿著一根長杆,杆那一頭挑著一個鳥籠。還有一個軍官手上什麼也沒拿。除了這群看上去多少有點超現實的人以外,還有珍妮特,她依然躺在當時倒下的地方。消防員已經把鉤子從我身上解開,伸向珍妮特。我站起身時他恰好鉤住她雨衣上的腰帶。他開始往這邊拉,腰帶果然斷了。於是他把鉤子伸到她離我們較遠的身側,推著她的身體朝我們這邊滾動。滾完第二圈,她坐了起來,看起來衣衫不整,而且非常憤怒。
“感覺還好嗎,蓋福德先生?”身邊有個聲音問。
我轉過頭去,認出那位軍官是艾倫·休斯,我們在澤拉比家見過他幾麵。
“還好。”我說,“這裏怎麼回事?”
他沒有立刻理會我的問題,隻把珍妮特從地上扶起來。然後他轉頭對那位下士說:
“我最好回到主路上去。你在這邊繼續,下士。”
“是,長官。”下士說。他沿垂直方向放低長杆,鳥籠仍搖搖晃晃地掛在杆的那頭。他小心翼翼地把籠子往前一伸。鳥從棲木上摔了下來,躺在鋪了沙子的籠底。下士收回籠子,鳥兒略帶憤怒地啾鳴一聲,又跳回棲木上站著。在旁觀的一名二等兵提著桶走上前去,在草地上塗上一個小小的白點;另一個二等兵在手中地圖上做了個標記。一行人又這樣走出十幾米,不斷地重複這番表演。
這次輪到珍妮特問這裏到底怎麼回事了。艾倫盡量解釋了他目前知道的一切,然後說:
“很明顯,隻要這種情況繼續,就不可能進去。你們最好的辦法就是去特雷恩等封鎖完全解除。”
我們望向下士一行人的背影,正趕上那隻鳥又一次從棲木上掉下來,然後他們繼續穿越通向米德維奇的無害田野。有了之前的經曆,我們明白似乎確實沒有其他可行的選擇了。珍妮特點點頭。於是我們謝過年輕的休斯上尉,與他作別,回頭走向我們停車的地方。
到了老鷹酒店,珍妮特堅持要訂一間房過夜,以防萬一……然後她上樓進房間休息去了,而我則向酒吧走去。
酒吧裏人滿為患,就中午而言這相當不尋常,而且裏麵幾乎全是陌生人。其中的大多數人,或兩人一對或幾人一組地聊天,情緒似乎有些激動;也有幾個人獨自若有所思地飲著酒。我費了些力氣才擠到吧台前麵。當我手裏端著酒往回走時,有個聲音越過我的肩頭對我說:
“啊,你怎麼會在這兒呢,理查德?”
這嗓音很熟悉,當我回頭看時,那張臉也很熟悉,盡管我花了一兩秒鐘才認出那是誰——因為我不僅要撥開幾十年歲月的麵紗,還得變戲法似的用想象給現在穿著花呢衣服的他帶上軍帽。可一旦認出他是誰,我便一下子高興起來。
“我親愛的伯納德!”我大聲喊道,“見到你太棒啦!來,讓我們找個地方單獨敘敘。”我抓住他的胳膊,把他往休息室裏拉。
一看到他,我就覺得自己又回到了年輕時代: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些海灘上,回到了阿登高原,回到了芮斯華森林,回到了萊茵河畔。我們聊得非常愉快。我向侍者又點了一輪酒。大約半個小時後,第一輪感情迸發才平靜下來。這時:
“你還沒有回答我剛才問你的第一個問題,”他一邊認真地看著我,一邊提醒道,“我一點也沒想到你會幹這一行。”
“哪一行?”我問道。
他微微抬起頭,望向吧台方向。
“媒體。”他解釋道。
“哦,原來那幫人是記者!我正琢磨從哪兒跑來這麼多人呢。”
他的一條眉毛稍稍落下了一點。
“嗯,如果你不是跟他們一夥的,那你來幹什麼?”他說。
“我隻是住在這附近。”我告訴他。
這時珍妮特走進了休息室。我把伯納德介紹給她。
“珍妮特,親愛的,這位是伯納德·韋斯科特。我和他在一起的時候他是韋斯科特上尉,但我知道他後來升了少校,而現在他已經是——”
“是上校了。”伯納德承認,然後以迷人的風度問候了珍妮特。
“見到你真高興,”珍妮特對他說,“我常聽他提起你。我知道有時候人們這麼說隻是客套,但我這句話可是真的。”
她邀請他與我們共進午餐,但他說他還有公事要辦,而且已經遲到了。他遺憾的語氣聽起來足夠真誠,於是她說:
“那就一起吃晚餐吧?去我們家吃,要是我們能回去的話。如果到時候我們還困在這裏,就在這裏一起吃?”
“你們家在哪兒?”伯納德問。
“在米德維奇。”她解釋道,“離這裏大概十三公裏遠。”
伯納德的態度稍稍改變了。
“你們住在米德維奇?”他一邊問,一邊把目光從她身上移到我身上,“搬到那裏很久了嗎?”
“大概一年了。”我告訴他,“正常情況下我們現在應該正在那兒,但是——”我解釋了我們困在老鷹酒店的前因後果。
我說完後他思考了一會兒,然後似乎終於做了決定。他轉向珍妮特,說:
“蓋福德太太,如果我帶走你丈夫,你會原諒我嗎?我到這兒來就是為了米德維奇的事情。我想他也許能幫我們,如果他願意的話。”
“你的意思是,幫你們調查發生了什麼事?”珍妮特問。
“這個嘛——可以說是和那有關吧。你怎麼想?”他又問我。
“要是我能幫上忙,我當然願意。但是我看不出……你說的‘我們’是誰?”我問。
“你先跟我走,路上再解釋。”他對我說,“其實我一小時前就該到那兒了。要不是事情實在重要,我不會這樣貿然把他拖走的,蓋福德太太,你一個人在這裏沒問題吧?”
珍妮特讓他放心,說老鷹酒店是個安全的地方。然後我們起身離座。
“還有一件事,”我們離開前,他又對珍妮特說,“別讓酒吧裏的任何人糾纏你。要是他們糾纏你,就直接叫他們走開。他們聽說自己的編輯不打算碰米德維奇的事,都有點鬧起脾氣來了。你不要對他們透露任何一個字。以後再跟你細說這事。”
“好的。我等不及要聽了,不過我會守口如瓶的。”我們離開時珍妮特這樣答應了。
在離受災區域稍有一段距離的地方已經建立了一個指揮總部,就在奧普雷路上。在警察看守的路障處,伯納德出示了一張通行證,執勤的警官向他敬了個禮,我們就這樣通過了,再沒遇到任何盤問。一位非常年輕的三星肩章軍人本來正悶悶不樂地獨自坐在帳篷裏,一看見我們就精神了起來。既然拉切爾上校外出巡視去了,他認為向我們介紹情況就是他的責任了。
籠中的鳥兒們這會兒似乎已經完成使命,被送回主人身邊去了,他們是出於公益精神才不情不願地出借愛鳥。
“皇家動物保護協會十有八九會來向我們抗議,要是鳥兒得了支氣管炎什麼的,估計還要找我們賠償損失。”上尉說,“但是實驗結果有了。”他拿出一張大型地圖,上麵畫著一個完美的圓圈,直徑約三公裏。米德維奇教堂就在圓心稍微偏東南一點的地方。
“就是這樣。”他解釋說,“就我們所知,受影響區域是整個圓內的所有地區,而不僅是圓周上的帶狀區域。我們在奧普雷教堂的塔樓上設了一個觀察哨,目前沒有在區域內觀察到任何活動——酒館外麵的路上躺著幾個人,也完全沒有動過。至於影響該區域的東西是什麼,我們沒取得什麼進展。
“我們已經明確,這種東西是靜止的,無形無味,雷達探測不到,不反射聲波,對哺乳動物、鳥類、爬行動物和昆蟲立刻起效。似乎還不會留下後遺症——至少沒什麼直接影響,盡管公共汽車上的人還有其他在裏麵待了一陣的人自然會有些不舒服。我們掌握的情況差不多就這些。至於那東西究竟是什麼,老實說,我們還沒有任何頭緒。”
伯納德又問了他幾個問題,但沒得到更多答案。於是我們動身去找拉切爾上校。過了一會兒,我們找到了上校,他正和一個年長的男人在一起,那人是溫郡的警察局長。兩人站在一個稍高的小土坡上觀察地形,身邊還有幾個級別較低的人陪著。這群人的姿態活像一幅十八世紀的版畫,畫的是一位將軍正在觀看一場戰況不太順利的戰鬥,唯一的區別是現在這幅畫上是場看不見的戰鬥。伯納德介紹了他自己和我。上校熱切而認真地看著他。
“啊!”他說,“啊,對。你就是電話裏的那個人,跟我說這事必須保密的那個。”
不等伯納德回答,警察局長就插話進來:
“保密!保密,可不是嗎!國土上有個三公裏的圈完全被這東西覆蓋了,而你卻叫我們保密。”
“這是上麵的指示。”伯納德說,“安全部門——”
“他媽的,他們認為該怎麼——”
拉切爾上校打斷了他,不讓他再說下去。
“我們已經盡力宣稱這是一次突擊戰術演習。雖然不太站得住腳,但好歹有個由頭可說。得有個由頭。麻煩的是,就我們目前知道的情況看,可能是我們自己搞的什麼小把戲出了問題。如今他媽的到處都是保密行動,沒有人知道任何事情。不知道其他人手裏有什麼,甚至不知道你自己可能得用上什麼東西。那麼多在後麵搗鼓的科學家要把我們這個行業毀了。你沒法跟上你都不知道是什麼的東西。軍人這行很快就隻剩巫術和電線了。”
“新聞機構已經在關注這事了,”警察局長不高興地抱怨道,“我們趕走了一部分人。但是你也知道新聞記者是什麼樣的,他們肯定還會想辦法在周圍探頭探腦,得把他們揪出來趕走。你打算怎麼叫他們替你保密?”
“這個,至少不需要你太擔心,”伯納德對他說,“內政部已經對此事下了一條通知。他們讓人惱火,但我覺得他們發話還是管用的。不過媒體是否會報道,還是取決於這事會不會引起足夠的轟動,讓媒體覺得值得來找麻煩。”
“嗯,”上校邊說邊再次望向前方沉悶的風景,“我想那取決於從報社的角度看,這位‘睡美人’是會轟動一時,還是會無人問津。”
在接下來的一兩個小時裏,不斷有各式各樣的人跑來,明顯都是各個部門的代表,有來自軍事部門的,也有來自非軍事部門的。奧普雷路邊支起了一頂更大的帳篷,一場會議於十六時三十分在帳篷裏召開。拉切爾上校首先發言,梳理了目前的情況。這通講話用時不長。講話收尾時來了一位空軍上尉。他惡狠狠地衝進來,把一張照片拍在上校麵前的桌子上。
“瞧好了,各位先生。”他很不高興地說,“為了這張照片,我們損失了兩個好人和一架飛機,幸好另一架沒事。我希望這種損失是值得的。”
我們圍上去看桌上的照片,並和地圖比較。
“那是什麼?”一位情報部門的少校指著照片上的一個東西。
他指的那個東西看上去有蒼白的橢圓形輪廓,從周圍的陰影判斷,形狀有點像一個倒置的勺子頭。警長彎下腰來,更仔細地看那個部分。
“我看不出來那是什麼,”他承認道,“看起來可能是某種不尋常的建築物——但那裏不可能有什麼建築。我不到一周前剛親自去過修道院廢墟周圍,當時那裏沒有任何東西。而且,那塊地屬於英國文化遺產保護局。他們隻負責讓已經有的東西不倒,不會新建任何東西。”
另一位與會者從照片看向地圖,又從地圖看向照片。
“不管那是什麼東西, 數學上看這東西正好在問題區域的圓心上。”他指出,“要是幾天前它還不在那裏,那麼肯定是某個東西在那裏著陸了。”
“也可能那是個幹草堆,上麵套了個顏色很淺的罩子。”有人提議。
警察局長不屑地哼了一聲:“看看這個大小,夥計——還有這個形狀。幹草堆的話得有十幾個才有這麼大,至少得十幾個。”
“那這到底是個什麼鬼東西?”少校問。
我們一個接一個用放大鏡研究那個東西。
“你們不能從更低空拍一張照片嗎?”少校提議。
“要不是因為我們試過,怎麼會損失一架飛機?”空軍上尉粗暴地對他說。
“這個——該叫什麼——這個受影響的區域向上延伸到多遠的地方?”有人問。
空軍上尉聳聳肩。“你要想知道可以朝裏麵飛啊,”他邊說邊用手指敲著照片,“這張是在上方三千米拍的。機組人員在那裏沒發現任何影響。”
拉切爾上校清了清嗓子。
“我手下有兩名軍官提出,這個區域可能是個半球體。”他說。
“有可能,” 空軍上尉表示讚同,“但也可能是斜長方體或者十二麵體。”
“我是這麼看的,”上校溫和地說,“他們觀察了鳥兒飛進那個區域的情況,記下了鳥兒開始受影響的精確位置。據他們說,區域邊緣不是像一堵牆那樣垂直向上延伸的,這一點已經明確了——所以事實上這個區域肯定不是圓柱體,側麵是微微向裏收縮的。因此他們認為,受影響的範圍要麼是圓穹形的,要麼是圓錐形的。他們說他們收集到的證據更傾向於半球體,但是這個弧太大了,他們隻能研究其中一小部分,所以不能確定。”
“嗯,你提出的是這段時間以來我們唯一的收獲。” 空軍上尉承認。他思考了一會兒,又說:“如果他們關於半球體的說法正確,那麼影響範圍最高在圓心上方大概一千五百米。但怎麼才能確認這一點而不再損失一架飛機,我估計他們也沒什麼有用的主意。”
“事實上,” 拉切爾上校不大有信心地說,“其中一個人有個主意。他建議,我們也許可以弄一架直升機,下方用幾十米長的繩子掛一個裝金絲雀的籠子,然後緩慢地降低高度——嗯,我知道這聽上去——”
“不,” 空軍上尉說,“這是個好主意。聽上去就是確定邊界形狀的那個家夥想出來的吧。”
“沒錯,就是他。” 拉切爾上校點點頭。
“他在鳥類軍事科學方麵很有自己的一套啊。” 空軍上尉評論道,“我認為金絲雀的點子我們可以再修改提高一下,但是我們很感謝他提供了這個想法。今天有點太晚了,我會在明天清晨安排的,趁光線好的時候從最低安全高度再拍些照片。”
情報部門的那位少校突然打破了沉默。
“我認為需要備些炸彈。”他沉思著說,“碎片殺傷炸彈,也許。”
“炸彈?”空軍上尉邊問邊挑起眉毛。
“準備一些不會有什麼害處。你永遠不知道那些俄國人想搞什麼鬼。不管怎麼樣,狠狠炸它一下可能是個好主意。這樣它就跑不了了。先把它炸暈,我們才好仔細研究。”
“現在這個階段就這麼搞有點太激進了,”警察局長提出,“我的意思是,如果可能的話,還是先讓它保持完整比較好吧?”
“的確可能如此,”那位少校表示讚同,“但這樣隻會放任它繼續幹它想幹的事,而且它會繼續用那玩意兒阻止我們靠近,不管那玩意兒是什麼。”
“我看不出它跑到米德維奇來能幹些什麼。”另一位軍官插了嘴,“所以,我猜測它隻是迫降在這裏,然後用這種屏蔽阻止我們幹預,好爭取時間維修。”
“這裏有格蘭奇研究所……”有人以試探的口氣說。
“無論是哪種情況,我們越快獲得權限進一步破壞它的功能越好。”少校說,“不管怎麼說,它也無權侵入我們的領地。當然,真正的重點是,絕不能讓它跑了。它太有意思了。除了那玩意兒本身,它的屏蔽效果能為我們所用的話就更好了。我建議采取一切必要行動獲取它,盡可能讓它保持完整,但如果必須破壞的話也不用手軟。”
大家進行了不少討論,但沒得到多少結果,因為在場的每個人幾乎都隻是來觀察和彙報情況的。我能記起來的唯一實際的決策,是夜間每小時投放帶降落傘的照明彈,以方便觀察,還有清晨派直升機嘗試拍攝更有信息量的照片。除此之外,散會時並沒有取得其他明確進展。
我不明白伯納德為什麼把我拉到那裏——事實上,我甚至不明白他自己為什麼要參加那次會議,因為整個會議期間他沒做任何貢獻。開車回去的路上,我問他:
“我能問問你為什麼要摻和這事嗎?我這樣問會不會太冒犯了?”
“也不算冒犯。我對這事有職業上的興趣。”
“因為格蘭奇研究所?”我試探地問。
“是的。格蘭奇研究所在我負責的範圍內,所以我們自然對周圍發生的所有不尋常的事都有興趣。這件事,應該可以說是非常不尋常了吧,你不這麼覺得嗎?”
我已經從他會前的自我介紹中猜出,他說的“我們”要麼是泛指整個軍事情報部門,要麼是特指他供職的具體部門。
“我還以為,”我說,“這種事情是由特殊機構負責的呢。”
“不同的機構負責不同層麵的事務。”他含糊地回答,然後就轉移了話題。
經過一番努力,我們總算在老鷹酒店給他訂到一間房。然後我們三人一起用了晚餐。我本來希望飯後他能兌現“之後細說”的承諾,結果我們雖然談了不少事情(其中包括米德維奇的情況),他卻顯然有意避免再談他對此事的職業興趣。盡管如此,我們仍然度過了一個愉快的夜晚,我甚至開始想,怎麼會粗心到讓一個像他這麼好的朋友淡出我的生活呢?
那天晚上,在談話的間隙,我兩次致電特雷恩警方,詢問米德維奇的狀況可有改變。兩次對方都說情況基本沒變。打完第二通電話,我們認定再等下去也沒用,於是喝完最後一輪酒就回房休息了。
“他人真好。”房門一關,珍妮特就說,“我本來擔心你們在一起會變成老兵重聚,那太太們在一邊可就無聊透了。但他沒有隻顧著談那些。今天下午他為什麼要帶你一起去呢?”
“我也覺得很奇怪。”我坦白道,“等我們真到了那裏,他似乎就改了主意,不願再向我透露更多內情了。”
“這可真是太奇怪了。”珍妮特說,好像剛剛才重新意識到整件事有多不正常,“到底是怎麼回事?他真的一丁點兒都沒告訴你嗎?”
“不僅他沒說,其他人也都沒說。”我向她保證,“他們隻知道一件事,還是我們告訴他們的——你完全不知道那玩意兒是怎麼擊中你的,事後也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它曾經擊倒過你。”
“能明確這一點至少也算有點眉目。希望村裏的人都和我們一樣安然無恙吧。”她說。
二十八日早晨,當我們還在熟睡時,一名氣象官員認為米德維奇的地麵低霧會提前散去。於是,兩名機組人員登上一架直升機,接著有人遞給他們一個鐵絲籠,裏麵裝著一對活潑而困惑的雪貂。然後,飛機起飛,吵鬧地騰空而起。
“據他們估計,”飛行員說,“一千八百米絕對安全,所以我們先飛到兩千一百米試試看。討個好彩頭。如果沒問題,我們再慢慢把它們降下去。”
旁邊的偵查員放下設備,忙著逗兩隻雪貂玩,直到飛行員對他說:
“好,你可以把籠子放下去了。我們七點整開始穿越試飛。”
籠子伸到了門外。偵察員把線放出九十米長。飛機掉了個頭,飛行員通知地麵,他即將開始進行第一次橫穿米德維奇的飛行。偵察員趴在地上,透過鏡片觀察籠中的雪貂。
目前它們情況良好,不停地在籠子裏爬來爬去,還撲到對方身上。他把望遠鏡從雪貂身上移開了一小會兒,望向前方的村子。
“喂,機長。”他說。
“嗯?”
“他們叫我們拍的那個東西,修道院旁邊的那個。”
“它怎麼了?”
“嗯,要麼它隻是個幻影,要麼它現在飛走了。”偵查員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