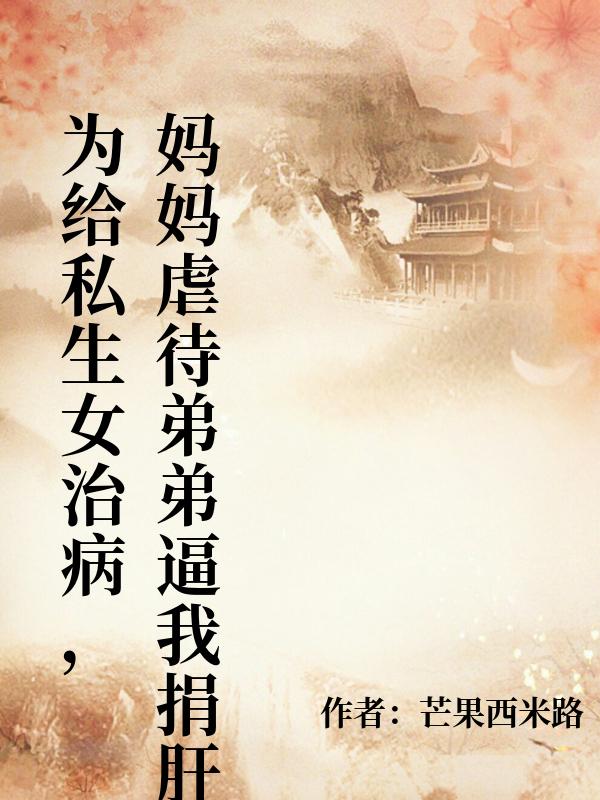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一章
媽媽有兩個女兒,一個是和白月光初戀生下的孟諾,一個是我。
我的肝也一分為二,左葉給了媽媽,右葉給了孟諾。
三年後,孟諾病情不穩定,需要二次肝移植手術時,媽媽來到我的出租屋裏。
忍著嫌惡,她在屋子裏四處搜尋,最後隻看到十六歲癡傻的弟弟。
她拿出棒棒糖誘哄著許思彥說出我的下落,卻被徹底無視,隨即開出條件:“許晴,隻要你答應再給諾諾捐肝,我就承認你和思彥是我的孩子!”
弟弟從桌角抽出我的死亡證明遞了過去,一臉平靜:“媽媽,姐姐再也捐不了肝了。”
孟霜將整個出租屋從裏到外翻了個底朝天,還是沒看到我的身影。
她麵色一變,狠狠地踹倒瘸了一隻腿的木桌,視線落在蹲在地上啃爛蘋果的弟弟身上。
“思彥呀,姐姐去哪了?媽媽手裏有棒棒糖,隻要你帶我找到她,這根棒棒糖就是你的!”
看著弟弟充耳不聞的樣子,媽媽氣得奪過蘋果,狠狠地踩上兩腳。
“都什麼時候了,還吃,諾諾還等著救命呢,快說,你姐姐在哪!”
我看著這一切,內心湧起一陣酸澀。
媽媽還是跟記憶中一般貌美,和麵黃肌瘦的弟弟形成鮮明的反差。
看著她為難弟弟,我多想開口,可我做不到了。
我死了,死在三年前給孟諾移植肝的手術中,而媽媽對此一無所知。
弟弟被嚇得要躲進臥室,卻被孟霜一把揪住,狠狠地打在了後背上。
“問你話呢,你是傻子又不是啞巴,跟你那沒出息的爸一個樣,老實交代,你姐姐呢?”
弟弟眼珠子轉了轉,極為自然地從桌角抽出皺巴巴的死亡證明,遞給孟霜。
“媽媽,姐姐死了,再也捐不了肝!”
孟霜看著殘缺不全的死亡證明,怒氣湧上心頭,一臉恨鐵不成鋼看向弟弟。
“許思彥,你姐姐怎麼教你的,連偽造死亡證明都不知道偽造像點的。我怎麼會有你們這兩個蠢到無可救藥的女兒和兒子,我看都是遺傳你那個廢物爸的智商!”
我想辯解,爸爸最愛我和弟弟,隻是六年前爸爸就因公殉職了。
爸爸葬禮的第二天,媽媽堂而皇之地將許諾迎了回來,僅僅比我小一歲。
她當著孟家所有人的麵承認孟諾的身份,更是告誡我和弟弟:“許晴,看好你弟弟,要是你們要是敢欺負諾諾,別怪我不客氣!”
盡管再不喜,我和弟弟都沒有做出傷害孟諾的事,她卻一而再再而三地刁難我們。
先是向媽媽告狀說我弄壞了她的裙子,再是買通保姆說我想在她碗裏下毒。
最後為了能把我們趕出去,更是造謠弟弟猥褻她,哭得要自殺。
媽媽氣得將我和弟弟痛打一頓,連同幾件破衣服,一同丟出家門。
沒辦法,我隻能放棄學業,早早打起零工,租了間出租屋。
第二年,更是一把付清了未來五年的租金,這才讓我和弟弟有個長久的住所。
而媽媽,一次都沒看過我們,放任我和弟弟自生自滅。
看著弟弟躺在地上喊痛,孟霜的臉色總算柔和些:“思彥,乖,告訴媽媽姐姐去哪了,你諾諾姐姐在醫院呢,情況很危急,懂事點。”
弟弟猛地撥開媽媽的手,大喊著不要去醫院,不要去醫院。
媽媽氣得踢了弟弟兩腳,鄙夷地開口:“許思彥,許晴就是這樣教你的,諾諾可是你親姐姐,你不讓去醫院是想害死她嗎?”
我克製不住淚水,想開口跟媽媽解釋。
弟弟隻是因為我在醫院死了,從此對醫院有了恐懼,可媽媽再也聽不到了。
弟弟捂著作痛的小腹,哭喊著:“你不是我媽媽,我媽媽不會這樣對我們,我隻有姐姐,隻有姐姐!”
孟霜被說得一愣,還想再發怒,弟弟已經把用力門關上。
孟霜狠狠踹了門幾腳,音量加大了些:“好,許思彥,既然你和許晴存心不想救諾諾,給我等著,再給你一晚時間。”
“明天早上,我再見不到許晴,你就替她給諾諾捐肝,看你們以後還敢不敢忤逆我!”
弟弟卻聽不到了,我眼睜睜地看著他暈倒在門後。
看著弟弟菜色般的臉,我鼻子一酸。
自從我去世後,沒了收入來源,很多時候弟弟隻能外出乞討撿垃圾為生。
孟霜剛才踩臟的爛蘋果就是弟弟今早上去垃圾桶裏撿來的,這也是弟弟一天的食物。
我看著地上一動不動的弟弟,拚命地想要弄醒他,可依舊是徒勞。
我都忘了,我一個靈魂,隨時都可以消散,怎麼能幫弟弟呢?
不知過了多久,弟弟悠悠轉醒,視線落在我所在的地方,而後很快移開。
我以為弟弟發現了我,沒想到他徑直越過我,走到沙發下,拿起那隻缺了耳朵的泰迪熊玩偶。
這是爸爸去世前給我和弟弟買的,一人一個,我的是粉色,弟弟的是藍色。
我的那隻早就被孟諾吩咐狼狗咬碎,弟弟的這隻即便被我死死護著,還是被咬掉隻耳朵。
弟弟將玩偶放在懷裏,一遍遍撫摸著早已不光滑的毛,淚水無聲落下。
“爸爸,姐姐,我好想你們,你們在哪裏,媽媽好凶…好凶…”
我想抱住弟弟,看著自己透明的身體,喉嚨澀得生疼。
整整一夜,我陪著弟弟從天黑到天明,看著弟弟滿臉的淚痕。
砰咚一聲,孟霜帶著人闖進了家門,看見弟弟還在睡著,氣得將碗筷一摔。
“還有心思睡覺,來人,給我潑醒他,我倒要看看,許晴會不會出來!”
弟弟被潑醒,全身濕漉漉的,狼狽至極,看見媽媽,掙紮起來:“姐姐死了,都是那個壞諾諾害的,都是她!”
孟霜氣得奪過弟弟懷中的玩偶,一巴掌打得弟弟腦袋嗡嗡。
“許思彥,還敢罵諾諾,幾年不見,你倒是變得牙尖嘴利了,看我不好好磨磨你的銳氣!”
一聲令下,孟霜帶來的保鏢將出租屋裏的東西打雜一空,沙發劃爛掀個麵,床更是被弄散架。
孟霜覺得還不夠,攥住弟弟的手腕,威脅道:“念在你是我兒子的份上,我再問一次,許晴在哪?諾諾的病情已經等不及了。”
弟弟一個勁地搖頭,說我已經死了,被媽媽猛拍了下頭,痛得弟弟流出鼻血。
“還撒謊,許晴可是把你看得跟眼珠子一樣重要,你肯定知道許晴在哪!”
弟弟雙手滿是血,痛得鼻涕淚水齊下,孟霜一愣,還沒想好怎麼開口。
弟弟爭辯:“姐姐死了,我也不想活了,我要去陪爸爸和姐姐了,你拿我的肝吧,別去折騰姐姐了。”
媽媽別開了眼,看著弟弟下半張臉都是血,掏出手帕想遞過去,卻被孟諾喊住。
她從豪車上下來,一副弱不禁風的樣子,挽住孟霜的胳膊。
“媽媽,我好疼,好疼......醫生說我如果不立刻手術,再也見不到媽媽了!”
“媽媽,你不要為難姐姐和弟弟了,讓諾諾去死吧,諾諾有這麼好的媽媽,已經很幸福了。”
孟霜心疼地摟緊孟諾,愛憐般地吻了吻她眉心,給我早已關機的手機打去電話。
接不通她又不死心地發去短信,一分鐘,五分鐘,兩個小時過去,依舊沒有動靜。
孟霜氣得將手機摔爛,握緊孟諾的手:“諾諾別怕,許晴不願意救你,媽媽就讓許思彥救你,媽媽不許諾諾寶貝這樣說!”
在看到地上癱倒的弟弟,媽媽臉上的溫柔瞬間被厭惡代替:“把他給我帶上車去醫院,先去檢查配型!”
“至於許晴,繼續找,把整個市掀翻了天都要給我找到!”
冰冷的白色床單上,弟弟痛苦的蜷縮著,左手血管反複抽血。
一旁的醫生看著心電圖和胸部X片,止不住地搖頭。
“孟女士,這個孩子身體太差了,而且血型也匹配不上。這樣無休止地抽血也是折磨,不如讓孟諾小姐再等等,說不定會出現合適的肝源......”
孟霜麵色冰冷,像是對醫生說,又像是對床上痛得手背青筋暴起的弟弟說。
“我也不想為難他,明明隻要他說出他姐姐的下落就好,偏偏他嘴硬要硬撐。”
“記住,每天抽他400cc,留著他一口氣,我倒要看看是他倔,還是我這個媽媽的手段更硬。”
孟霜摔門而出,醫生也沒辦法,看著床上的弟弟長歎了口氣。
整整三天,弟弟一直陷入眩暈之中,看著汩汩的鮮血流出,我的心痛不可遏。
給弟弟抽血打針的護士已經麻木,弟弟手背上的針頭越來越多,孟霜卻依舊沒來。
等到第四天弟弟不幸發炎,戴上呼吸機時,孟霜踩著高跟鞋姍姍來遲。
或許是弟弟憔悴的模樣引起她內心的愛憐,孟霜語氣和緩了點:“這幾天苦頭吃夠了吧,媽媽也不想真的為難你,說清楚你姐姐在哪,媽媽就放了你。”
“而且媽媽隻是讓許晴那丫頭捐肝。媽媽知道,距離上次捐肝手術已經三年了,她早就恢複了,壓根不會有什麼危險的。”
弟弟身子一僵,嗚咽地開口:“沒了,沒了,姐姐沒了,肝都給你和那個壞姐姐了......”
孟霜被弟弟的話弄得一頭霧水,還沒問清楚,弟弟猛地吐出一口鮮血,醫生匆忙進行急救。
病房外的孟霜反複思索著弟弟的話,不知不覺走到孟諾的病房。
給她端上精心煲煮的粥後,孟霜決定問問:“諾諾,你還記不記得許晴第一次給你捐肝的手術,當時醫生怎麼說的?”
孟諾眼裏一閃而過驚訝,很快掩飾好,親昵地靠在孟諾懷裏。
“媽媽,你這是擔心什麼,當初那手術可是我爸爸的老朋友做的,這有什麼不放心的。”
“我爸爸去世的早,要不是他們和媽媽,諾諾怎麼會有現在這麼幸福的生活。”
看著二人母女情深的樣子,我十指深陷掌心。
孟諾第一次肝移植前的兩個月,孟霜因為長期應酬加上酗酒,肝功能衰竭,生命垂危。
看著她生命垂危,遲遲等不來肝源,我挺身而出捐贈了左葉肝臟。
手術後不到半日,我便被孟諾的人趕出醫院,自此落下後遺症。
直到反複的暈倒,腹部的傷口反複滲血,我才明白是術後感染。
還沒等到去醫院,媽媽就以弟弟要挾我為孟諾捐肝。
我想告訴媽媽實情,孟諾卻拿出弟弟在家的照片威脅我上了手術台。
冰涼的手術刀在身體內反複進出,麻藥藥效早已過了,我反複承擔著痛苦,全身都在發抖。
卻沒想到孟諾根本沒想讓我活著,她安排好的人還沒等手術結束便將我扔回出租屋了事。
生命的最後,我看到弟弟哭得泣不成聲,想安慰他,卻連一句完整的話都說不出來。
眼皮越來越沉重,我眼前浮現弟弟九歲前爸爸還沒犧牲時一家人幸福的模樣。
媽媽會親手為我和弟弟製作小餅幹,即便工作再忙,總會抽出時間陪我們。
而爸爸會主動說起他抓壞人的經過,用一個個精彩的小故事哄我們入睡。
可自從孟諾被接回來後,一切都變了,媽媽對我們越發嚴厲,選擇無條件偏向孟諾。
現在為了孟諾,還要為難從小心智不全的弟弟,隻為讓我再次捐肝。
不知過了多久,醫生那邊傳來弟弟脫離危險的好消息,媽媽臉上卻不見笑容。
“既然沒死,那就繼續加大抽血量,一天600cc,我看看他說不說!”
弟弟臉色越發蒼白,全身瘦的隻剩骷髏架了。
醫生實在看不下去,勸了孟霜兩句,卻被媽媽投訴直接辭退。
媽媽看著病床上雙目呆滯,臉頰烏黑泛紫的弟弟,再次開口:“你編的那些話我都核實過了,許晴也真是費心了,還教你這麼多謊話。”
“你也不看看,這麼多天,她連一次都沒來看過你,你為她這麼做值得嗎?”
弟弟死死盯著天花板,沒出聲,左手小幅度動著。
媽媽走到弟弟身前 看清了那是之前他拿出的死亡證明,撫了撫眉心。
“都說了,就算要偽造你也偽造個像的,你看看這都爛成這個樣子,上麵的署名......”
媽媽話還沒說完,弟弟拉住媽媽的手,搖搖頭,有氣無力:“不是,是......是真的......”
“姐姐和爸爸都愛…思彥......媽媽不愛!”
弟弟說完,再也忍不住,一口血接著一口血吐,媽媽的胸前被血漬浸染,嚇得退後一步。
醫生護士輪番上陣,電擊除顫人工呼吸幾番操作下,弟弟的生命特征趨於穩定。
一牆之隔的媽媽攥著泛黃的紙張,看著秘書發來依舊一無所獲的消息,更加煩躁。
她腦海裏反複回蕩著弟弟的話,將那張死亡證明拍照發給了秘書。
“快去幫我核實,一天之內,我要知道這張證明的真假!”
做完一切,媽媽無力地癱倒在地,腦海裏浮現出我死不瞑目的樣子,嚇得一叫。
她連忙起身回到孟諾的病房,不由分說地摟緊她,撫摸著她的頭發。
“諾諾再等等媽媽,思彥那小子就是不說,媽媽已經加大人手去找許晴了,放心!”
孟諾遮住眼底的寒意,同樣回摟住孟霜:“我知道媽媽,有你在諾諾很開心,即使現在讓諾諾去死,諾諾都願意。”
這句話卻突然觸碰了媽媽的神經,媽媽猛地一驚,臉上浮現一絲郝色。
我看著她,輕笑一聲,原來她也終於意識到了不對勁。
正怔愣時,負責看護弟弟的醫生猛推開門,氣喘籲籲:“孟女士,那孩子不見了,通過監控,我們發現他去了天台!”
媽媽著急地小跑到天台,一路上 她腦海裏反複出現弟弟的那幾句話。
等看到弟弟穿著空蕩蕩的病號服站在天台邊的時候,她徹底慌了。
“思彥,有什麼你下來好好說,媽媽在這,快回來......”
弟弟固執地搖搖頭,指著媽媽和她身旁的孟諾:“你們......都是壞人,我不要你們了,我要去找爸爸和姐姐......”
弟弟又向陽台邁進一步,看得在場所有人心一揪,媽媽更是麵上不忍。
我想攔著他,弟弟卻朝我所在的方向看了我一眼,露出個笑:“姐姐......思彥是不是很沒用......思彥要去找你了,你和爸爸要等我......”
我以最快的速度衝向弟弟,卻是徒勞,隻看到他的身影撲通落下去。
媽媽幾乎是目呲欲裂,撕心裂肺地喊了句:“思彥,回來!”
一陣風吹過,媽媽從地上爬起來,想越過警戒線,卻被警察死死攔住。
秘書一路跌跌撞撞地跑上天台,停在媽媽身邊,顫顫巍巍地開口:“孟總,那份死亡證明是......是許晴小姐的,去世時間是三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