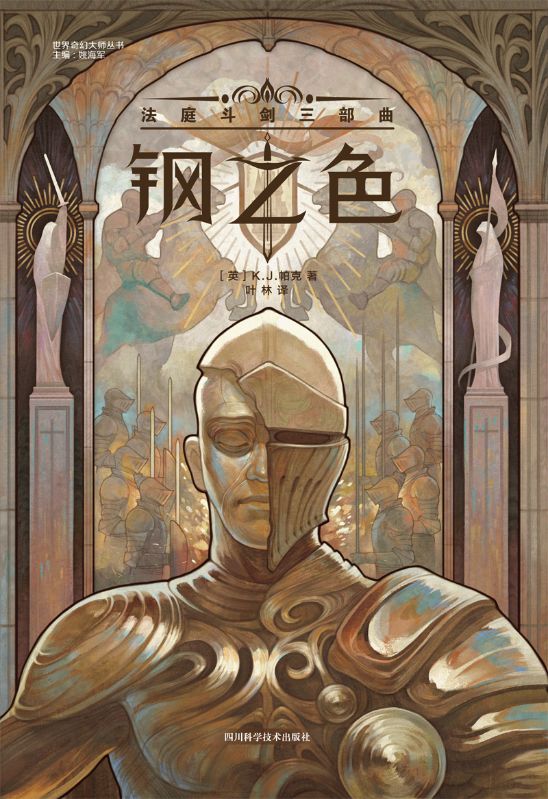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四
“你在看什麼?”工程師詢問道。
特姆萊退後幾步。“對不起,”他說,“我隻是看看。”
工程師沉下臉來,往鋸木屑裏吐了口唾沫。“難道你手頭沒活可幹嗎?”
“我幹完手頭的活了,在等下一批毛坯。想趁這個時間處轉轉。”
工程師嘟囔著回去幹自己的活了。他正在忙活的是一架小型重力投石機的框架,就是可以拋擲一百擔石頭的那種機器。此時,他正在用一把鑿子和一個山毛櫸木槌,在一塊十二尺長的厚木板上鑿出燕尾榫。這塊厚木板是之前他和另一個人用一把十尺長的鋸子從一根粗大的陳年白蠟木上鋸下來的。
“這是主支架的一部分吧?”特姆萊問道。工程師有些驚訝地抬起頭。
“人字架的左半邊。”他回答道,“右半邊已經打造好了。你怎麼懂這麼多機械知識?”
“我感興趣。”特姆萊說,“我一直在觀察。”
工程師點點頭,他的胸口長滿又粗又濃的白色胸毛,胳膊像熊一樣粗壯。“我認得你,”他說,“你是那個新來的小子,那個草原人。”他嘴角抽動,露出一絲微笑,“我猜你在草原上看不到這些吧。”
“是啊。”特姆萊說,“看到這麼多不同的機械設備,我覺得太神奇了。”
工程師忍不住大笑起來。“這些不算什麼,”他說,“重力投石機的設計原理很淺顯。你隻需要在一頭放上死沉死沉的配重,另一頭掛一個可以放石頭的吊兜,它就可以繞著由兩個人字架支撐起來的樞軸轉動。然後,你用絞車把配重吊起來,另一頭裝上石頭。一放手,配重落下來,石頭拋出去。簡單得很。和我們這裏製造的其他機械比起來,根本不值一提。”
“噢,”特姆萊說,“我覺得它們相當高明。”
工程師聳聳肩,“性能的確不錯。毫不誇張地說,我們這裏造的投石機可以將四百擔重的石頭拋出三百五十碼(1)以外。這架隻是小意思,拋擲距離相同,但隻有四分之一的承重。”
特姆萊感激地點點頭。看到他眼中的熱忱,工程師心裏很受用。真正的工程師全都是滿懷激情的人。像畫家和雕塑家一樣,他們也渴望得到別人的崇拜和尊重,而且他們知道,自己該得到的遠不止如此。一個雕塑隻要看起來像模像樣就可以,而一台機器卻必須能夠運作。
“你們怎麼知道該造多大的機器呢?”特姆萊問道。
工程師再次哈哈大笑起來,不過並沒有惡意。“我的孩子,這是個相當好的問題。有些你可以通過計算來決定,我們管它叫公式。其餘的,隻能通過不斷的試驗和不斷的出錯來獲得經驗。你先造一個,看看行不行。不行就換個方式再造一個,就這樣不停地試下去,直到造出一個能用的。我們管這叫原型機。”
“啊——”特姆萊說。
“舉個例子,”工程師一邊仔細畫好需要用鑿子輕輕敲擊的長方形區域,一邊說道,“軍械部長來找我,說他們剛剛在從長恩到這裏的海堤上建了五座堡壘,需要我們供應十架輕型投石機。他把對投石機的要求告訴我,於是我開始思考。我們曾經造過一架拋杆長三十三尺、配重一萬擔的投石機,可以將五十擔的石頭拋出兩百碼遠。就投石機而言,這型號算是小意思,和小孩的玩具差不多。但可以以此為基礎來設計。我是這樣考慮的:三十三尺拋杆、一萬擔配重,可以讓五十磅(2)的石頭飛出兩百碼遠。如果要把一百磅的石頭拋出三百五十碼以外,我可以先試試四十尺的拋杆加一萬五千擔的配重。然後,我忽然想到,等等,我以前還造過一架五十尺拋杆、兩萬五千擔配重的投石機,可以將三百擔重的石頭拋出二百七十五碼。因此,我決定先試一下四十尺拋杆加一萬擔配重,如果拋杆斷了,那我就知道四十尺的拋杆對於一萬擔配重來說太長了,於是嘗試三十六尺拋杆。既然拋杆變短了,那麼就需要增加另一頭配重,因此我把它加到一萬七千擔。如果拋杆撐不住,就需要加粗,剛才的那些數據就沒用了。”他停下來歇了口氣。“製造機器,”他說,“急不得。”
“太複雜了。”特姆萊說。他聽起來有點灰心喪氣,工程師忍不住露出微笑。
“造出能用的機器,”他說,“確實是相當複雜的過程。不能用的東西,隨便哪個該死的傻瓜都能做。無意冒犯,孩子,但你們外邦人就是這樣。你們看到一個機械設備,就覺得這是個好主意,我們也做一個。可你們從來不停下來思考尺寸和材料。等發現不能用了,你們就說,去他的,哎呀呀,神明發怒了。就此甩手不幹。區別就在這兒,”他敲敲自己的前額,補充道,“這裏。”
“我明白了。”特姆萊回答道,“這就是你們都很聰明的原因。”他打量著一旁的部件——有的靠牆一溜兒擺開,有的被夾在特製的夾具中,還在製作中——同時嘴唇翕動,無聲地計算著。“我想不僅拋杆和配重很重要,”他繼續問道,“造出尺寸正確的支架也很重要吧。”
“你開始入門了。說不定我們能把你培養成一名工程師。”他拍拍麵前被粗大的鐵鉗固定在支架上的木料,“我一直在想,把支架做成12×8×12的尺寸,應該就差不多了。畢竟我不需要裝配那種能支撐起三萬五千擔配重、長六十尺的拋杆。你懂了吧?配重大,拋杆長,人字架也需要立得高。但是,支架的頂角越是尖銳,被壓垮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你必須給它更多的支撐。但就在這個時候,軍械部的某個笨蛋過來要求你減掉兩千擔的配重,不然準備安裝投石機的哨塔承受不了。”工程師誇張地翻著白眼,“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明白。除了投石機,你們還做什麼其他的機械?”
“應有盡有。”工程師自豪地說,“今年到目前為止,我已經做了射石車、彈弩、野驢砲(3)、弩砲、石弩,全是這類鬼東西。我可以告訴你,做這些精巧簡便的重力投石機可是個愉快的活兒。”
當特姆萊坐在自己的工作台前,小心將已淬過火的劍刃放在軟鋼芯上時,他不禁想起他的叔叔特斯萊。很多年前,他想方設法抓了一個佩裏美狄亞的製砲工匠,開始以極大的熱情以及各種別具特色的酷刑折磨他的俘虜,要他吐露製造戰爭機器的秘密。他折騰得越狠,效果越差,直到有一天他把俘虜弄死了,依然沒有套出半分秘密。這給草原部族留下了深深的困惑和敬意。在那之後,特斯萊宣稱要攻占這座城市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因為它的人民寧可麵對最慘烈的死法也不願背叛。當時特姆萊年僅十二,剛到可以參加議政會的年齡。他怯生生地指出也許他們用錯了方式。對於這些人,以拷問來獲得情報顯然是無用的。如果換個方式,直接向他們友好地詢問不行嗎?由於生怕自己被直接打發回去睡覺,他又急忙補充道,這些佩裏美狄亞人雖然傲氣十足,以城邦為榮,寧死也不會出賣它,但隻要問出正確的問題,讓他們有機會在無知的野蠻人麵前炫耀一下,沒準兒會輕易吐露實情。
五年後,他來到這裏。事實證明,用這種方式來套取情報比他想象的還要容易。現在他已經拿到了關於攻城塔、長梯、弩砲、重力攻城槌以及重力投石機的尺寸以及具體建造數據。而且隻是去了趟圖書館,看了本書,他就學到了侵蝕和破壞城牆的技術。在酒館認識的一名衛兵甚至帶他參觀了城牆和哨塔。他還和這名衛兵坐下來喝了幾杯,順便計算出換崗間隙以及當班的人數。由於在軍械廠工作,他對城市裏箭矢的儲存量以及生產能力的了解比衛兵隊長還要多。圖書館員還答應幫他找一本書,這本書描述了十種攻破防線、往城裏灌水的可行方案。二十年前它曾是軍事學院的必讀書,如今卻已經被大部分人遺忘。這是一本好書,和這座城市一樣,精彩、令人不安,還帶著一股子深藏的悲涼。
他將纏好的劍刃和鋼芯放進火中加熱焊接。他對此無比熟稔,從來不擔心失手。在當前的局勢下,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確保在危機到來的時候,城裏人至少有幾把用來自衛的寶劍。
準備付錢觀看阿爾維斯對洛雷登一案的人排成了長隊。隊伍中,有兩個人披著一模一樣、顏色和款式都已過時的鬥篷。一個是高瘦的年輕男子,另一個是個頭差不多高但身材有點圓潤的女孩。
(“我怎麼知道?上次我來這裏還是五年前。”
“你就沒想到時尚會變嗎?”
“老實說,沒有。”
“我的天哪!”)
他們的方言不僅不算粗俗,反而略顯古雅。排在後麵的人聽到之後互相捅捅對方,眨眼示意。島民,他們悄聲說,並誇張地檢查著自己的錢包是否還在。
“我不太確定要不要看這個。”檢票員從她手裏收走門口買的票,發給她一小塊骨籌,女孩壓低聲音說道,“看兩個成年人廝殺到底有什麼意思?”
她的雙胞胎哥哥搖搖頭。“他們很可能不會打太久。”他說,“更有可能出現的情況是一個殺了另一個,幹脆利落。”
“別裝傻,”他妹妹回答道,“我要說什麼你心知肚明。我認為這是一種野蠻的做法。”
她哥哥聳聳肩。“我不是在替他們辯解,”他說,“隻不過,你若想深入了解這群瘋子,你就得來看這個。”
“噓——他們會聽到你說的話。”
“啊,但他們聽不懂‘瘋子’這個詞(4)。聽著,你想加入公司,在這裏開展業務,就得對他們這種病態的司法係統改變態度。”他補充道,“有人問你的看法的時候,你必須說這是全世界最好的司法係統,明白嗎?”
女孩點點頭。“明白。”她說,“不過我還是搞不懂——”
“閉嘴。法官來了。我起立的時候,跟我一起站起來。”
“野蠻。”女孩從鼻子裏哼了一聲。
當海平麵上現出伸入雲端的白色冠冕時,佩裏美狄亞曾給她留下種種美好、浪漫的觀感。但在三重城待了三天以後,美好的印象破滅了。她仍然不適應這裏的氣味,也受不了這裏的街道。巨大的反差處處可見。市集攤頭擺著數不勝數的華服美衣以及布料,令人驚豔,顏色和質地更是島民們做夢也想不到的。但如果你穿著這些衣服上街,裏襯會在五分鐘之內被扯壞。這裏的建築,即使是在下城,也建得高大宏偉,可以和她老家王子的住處媲美。然而室外的街道卻滿是泥漿和穢物,踩下去咯吱作響。馬路上手推車和四輪馬車擁堵在一起,橫衝直撞,經常濺得過路行人一身汙水,就算躲在排水溝邊上,還是避不開直直撞過來的車子。街上的行人都穿著體麵,顯得很富足,但她注意到她的哥哥自始至終將佩劍明晃晃地掛在皮帶上,走路時避開門廊以及黑暗的巷道。她的結論是,這是一個旅行的好地方,但並不適合住下。
“看,辯護律師在那裏。”她的哥哥低呼一聲,伸出一根手指捅她。
(令她不適應的還有一件事:在家鄉,用手指指點點是一件很粗魯的事,但這裏人人都這樣做。剛來這兒的頭一天半裏,她尷尬得滿臉通紅。)
“這個是原告律師,那個是被告律師。”她哥哥繼續說道,“我想原告的律師更有名氣。”
“我不看。結束之後你跟我說吧。”
“隨你。”他往後一靠,想在石凳上坐得舒服點,同時四處張望,看看有沒有認識的人。
一開始,他並不情願在這趟旅途中帶上維特裏絲。但眼下她也沒製造出什麼麻煩,這讓他改變了主意。確實,由於她的緣故,晚間安排變得乏味了許多,但同時也免去了挺大一筆支出。她的衣食住行會花些錢,但總體算來還是省下了不少,倒也是好事。而且,不可否認的是,她確實對做生意大有幫助——在老家,漂亮臉蛋什麼作用都起不到,但這些自詡精明的佩裏美狄亞人看到女孩的淺笑和偶然露出的腳踝,簡直就像餓壞的鴿子見了穀子一樣。這一招以前在老家的時候他是萬萬不敢用的,畢竟在那裏,要是哪個男人不割斷和自己姐妹眉來眼去的陌生人的喉嚨,肯定會被當作懦夫。這兒就不一樣了,也沒什麼不好的,隻要維特裏絲別太習慣這種風氣……
照現在這速度,他將破天荒地在最短時間內完成任務。五分之四的酒和油已經出手了,賣了個好價錢。在亞麻、木材以及香料上賺的利潤隻有酒和油的一半,符合他的預期(也就是說,足以彌補他在兩千盞刺蝟形狀的油燈上犯的錯誤。也許該把這批貨在港口倒掉,為回程的貨物騰出位置)。現在他就隻缺兩樣貨物:掛鎖和螺栓。誰讓他運氣這麼差,恰好選在這兩種貨物都異常缺貨的時候來呢……
“發生了什麼事?”
“嗯?哦,抱歉,還早著呢。這一環節叫訴答程序,就是——”
“噓——”
他不好意思地轉頭道歉,接著降低音量繼續說道:“這一環節,他們要將案情陳述一遍。通常會有點專業——”
“為什麼?”
“什麼?”
“為什麼還需要陳述案情?我是說,如果最後的裁決是基於誰先把誰的腦漿打爆的話,陳述案情有什麼用?”
文納德聳聳肩,“我不知道,又不是我發明的這套司法係統。聽著,我不要求你認同,隻要了解大致的運作方式就行了。要做生意,最起碼要了解商業法的基礎。”
維特裏絲嗤之以鼻。“哼,”她說,“我認為這太荒唐了。”
“噓!”
案件陳述終於結束了,要不是石凳坐起來不太舒服,維特裏絲差點就睡著了。她一邊打嗬欠一邊眯起眼睛,看著下方兩名穿白襯衣的男子在法庭中央的決鬥場上互相試探,繞著對方打轉。顯然,高大的金發男子是熱門人物。因此,她決定給另外一位加油。
以島民的標準來看,他算是矮的,但在這些人當中算中等個頭。她的座位相當靠後,從這裏看過去,他比另一位年紀更大、個頭更矮,也更單薄。盡管如此,她還是不能理解為什麼所有人都認為他會輸。她的判斷剛好相反。在劍術方麵,她完全一竅不通,盡管文納德試圖解釋過幾句。在忍受了幾分鐘關於飛刺、自右向左劈、雙手劍之類的術語之後,她終於宣稱這聽起來跟曲棍球似的,隻不過更荒唐、更危險。的確,她一竅不通。但如果要她下注的話,她會賭矮的那個贏。她問過自己為什麼,最後認定是因為高的那個看起來很驕傲自大,也就是說,他很可能不夠謹慎。
我希望矮個子贏,她在心中默念。不為什麼。
戰況逐漸激烈。雙方停止了繞圈,開始刺向對方。維特裏絲忘了這件事有多麼荒唐,坐在她那窄小的位置上,興奮得身子直往前傾。她想為選手加油,就像在賽馬場一樣大喊大叫,但其他人全都沒動,安靜地坐著。這群人真是奇怪,去看表演卻不能喝彩有什麼意思呢?
“要不了多久就該結束了。”文納德擺出老手的篤定姿態低聲說道,“看,他感到疲勞了。”(維特裏絲心裏很清楚,他總共隻看過三場這類對決,但文納德就是這種德行,也許這就是他能在生意場上遊刃有餘的原因吧。)
維特裏絲觀察了一會兒,有點疑惑他們看的是不是同一場鬥劍。她不懂,也不想費神去了解劍術。但她認為,哥哥口中的疲倦,不過是矮一點的那個男人巧妙地搶占了決鬥場中央位置,讓另一個傻瓜消耗體力做各種動作而已。她不得不承認,這就是經驗和自負的對比。此時,高個子也不再以劍尖直刺,而選擇以劍刃劈砍。她認為這表示此人已經亂了章法了。是的,她也同樣認為,要不了多久決鬥就該結束了。
高個子朝著對方的腦袋劈出驚人一劍,對方立刻以既優雅又省力氣的方式擋了回去。維特裏絲很認同這個男人的行事風格。即使在那麼荒唐的情況下,也在盡量做到務實。要是對麵那個傻瓜再掉花槍,一不小心將自己的劍折成兩段,豈不是自作自受?
洛雷登心口一緊,意識到現在隻是時間問題了。他能感覺到,阿爾維斯認為自己已經贏定了。他的腦子對這場決鬥失去了興趣,已經放棄防禦,轉而依仗自己在速度、臂長以及力量上的優勢,攻擊時用劍刃多過劍尖。他知道洛雷登過於疲勞,很難發動有力的回擊,所以自己很安全。這點,洛雷登也心知肚明。結局在洛雷登被逼進場中央的那一刻就已注定。
洛雷登甚至不再去判斷對方的攻擊方位。他意識到,與其緊張地去判斷對方要從哪個位置劈砍,倒不如依靠本能來格擋。這麼多年鍛煉出來的條件反射是靠得住的,但也隻是將早已注定的結局延遲了一點。阿爾維斯遲早會用一個假動作來終結這場決鬥。
阿爾維斯假裝攻擊他的左上方,誘使洛雷登重心挪到後腳以反手格擋。他腳步剛挪到位就意識到自己上當了。對方真正要攻擊的是他的膝蓋,此時已經沒有任何回旋的餘地。該死,他平靜地想,感覺自己好像身在旁聽席而不是下麵的決鬥場,居高臨下地看著阿爾維斯的劍砍過來。危急關頭的本能反應讓他猛地扭過身來,左肩向前的同時右腿向後。對方的劍在距他膝蓋毫厘之外的空中劃過。十年的職業經驗讓他意識到阿爾維斯亂了陣腳,正是防守薄弱的時候。他沒時間看清,僅憑印象,朝阿爾維斯脖子的位置砍過去,同時祈禱自己沒有犯更大的錯誤。
他刺中了什麼。
首先要做的是脫離危險區——確認步法和身體的動作,拉開距離,劍撤回呈防守姿勢以後,才有餘暇看對方的頭是否還在。
頭還在的,但下巴一側有豆大的血珠湧出來。對方正在後退,以爭取時間以及安全的距離。洛雷登馬上挺身直刺。這是一個防禦動作,主要目的是刺激對方,讓他退得更遠。阿爾維斯的回擊有點笨拙。他怕痛,洛雷登意識到,真沒想到。他再次向前刺去,這一回比剛才認真得多。對方的回擊十分嫻熟,但仍處於守勢。此時,阿爾維斯已經退到了決鬥場中央。
就在這時,洛雷登想到了製勝招式。他第三次刺向前方,故意將左肩送出,讓自己的左半邊露出空當。這一招位置很低,阿爾維斯必然從上麵反擊。就在對方一劍刺來的時候,洛雷登迅速將後腳與前腳交叉,重心向右移,手中的劍垂到阿爾維斯的劍下方,希望這一係列動作能避過劍鋒。他感覺到有什麼東西劃過腹部,顧不上察看,揮手來了一記短劈。
他意識到自己上當了。
阿爾維斯手中的劍也畫了一個圈,隨即直劈下來。劍刃和洛雷登的頭骨之間沒有任何阻隔,唯一的辦法就是用劍柄的籠手擋一下,但那意義不大,因為下一劍……
沒有下一劍。
隨著一聲不大的脆響,阿爾維斯的劍斷了,斷掉的十八寸劍頭掠過洛雷登的臉頰。阿爾維斯的動作還在繼續,尚未完全意識到自己的劍斷了。洛雷登手腕一翻,對準阿爾維斯的臉部,刺出了短促而無力的一劍。這一刺看起來不痛不癢,甚至有點可笑,前提是阿爾維斯手裏的劍可以格擋。可惜沒有,洛雷登的劍尖直接戳進他的眼睛,瞬間殺了他。
“我們要鼓掌嗎?”維特裏絲倒抽了一口冷氣。
“不要。”
“哦。”
事情發展和她想的不太一樣。對手的劍在緊要關頭折斷,讓人覺得純粹是運氣不好,但她不這麼認為。毫無疑問,是他迫使對手做出注定會砍折劍尖的動作,否則他早就一劍將對方幹掉了。她放鬆下來,從口袋裏掏出一個蘋果。
目睹一個人當場斃命並沒有讓她感到驚恐不安,也許是因為她坐得太遠,看不到死者的麵部表情,也看不到血。坐在高高的看台上,下麵發生的一切就像一場遊戲,死去的人很可能根本沒死,隻是在裝死或是在表演。她不得不承認,這場表演很刺激,還好她從一開始就認定了贏家。不管怎麼說,現在她已經見識過佩裏美狄亞的訴訟案了,運氣好的話,她根本不用看第二場。為了僅僅四噸延誤交貨期的木炭,他們采取的解決方式顯得既粗俗又過分。
“我們可以走了嗎?”
“我們要等判決。”
“判決?但他已經……”
“怎麼回事?”
艾希莉的臉上帶著剛從一場混亂不堪的噩夢中驚醒的表情,臉色慘白。
他沒有回答。把劍遞給她時,才意識到自己忘了把劍擦拭一下。有什麼關係呢?
“怎麼回事?”她再次問道。
“什麼怎麼回事?”
艾希莉用力咽下一口口水。“剛才怎麼回事?”她追問道,“我還以為——”
“我也是。”洛雷登跌坐到椅子上,答道,“咱們可以不討論這個嗎?還有,行行好,幫我擋住那班混蛋。如果他們敢在這時候過來打擾我,我發誓我一定會殺了他們。”
艾希莉嚴厲地瞪了他一眼,匆匆趕去阻攔炭業公司的人。他們多半是來投訴的——因差點被殺而給客戶帶來緊張不適,結賬時應該打個百分之二十的折扣。這是個多好的借口啊。
他又想起阿爾維斯的斷劍。純粹是我的運氣,戰利品的三分之二成了破銅爛鐵,正如劍的主人一樣。誰能想到一把老舊軍用闊劍的籠手居然能磕斷一把質量上乘的司法用劍?他越想越疑惑,但沒有精力窮究不舍。
說起來真有意思,鋼條上的一個小瑕疵、小氣泡,或是在鐵匠錘子底下逃脫的一點沙礫或者其他什麼鬼玩意兒,居然能夠反轉結局、顛覆正義。他總覺得有什麼神秘力量在影響整個事件——一種細微得無法察覺的力量,一種不怎麼公平的力量。
也許,是我作弊了。他下了結論。
“我把他們打發走了。”艾希莉撲通一聲坐在他身邊,說道,“他們說——”
“我不想知道。”
艾希莉點點頭,“行。去痛飲幾杯?”
洛雷登搖搖頭。“我想找個地方躺一會兒。”他回答道,“然後我就不幹了。金盆洗手。”
“先去痛飲幾杯?”
“哎,好吧,大醉一場,然後我就徹底不幹了。”
“你知道嗎,”艾希莉一邊從白鑞酒壺裏倒酒出來一邊說道,“剛才我差點以為你說真的。”
“我剛才是認真的。”洛雷登回答道,“現在也是。”他換了隻手,按住壓在腹部傷口上的毛紡布。血早就不流了,多虧用了白蘭地清洗傷口,還敷了從酒館房梁垂掛下來的幾縷蜘蛛絲。但不知為什麼,他不想放鬆壓在傷口上的力道,總覺得這傷本該更嚴重。“我太老了,也沒什麼天賦。該轉行去做點別的了。”
艾希莉透過杯沿看向他,“比如?”
“我還沒想好。”洛雷登小心翼翼地從酒裏挑出一隻小蒼蠅,“最容易想到的就是,開一家劍術培訓學校。”
“當然,你可以開。”艾希莉回道,“但是,自己精通擊劍的動作不等於有能力教別人。”
“好吧,不是這個就是去做助理。你覺得我做助理怎麼樣?”
艾希莉搖搖頭。“你幹這行毫無希望。”她說,“首先,你會把所有的客戶都得罪光。再說,你根本不知道這行有多少苦活累活要幹。拿我自己做例子,我在天亮前一小時就起床了,在早飯前就寫了十二封信,然後去和客戶會麵,一直到來接你的時候。今天下午,我還有更多的信件要寫,還要處理賬目,草擬訴答文件——”
“好了好了,你已經說服我了。光是看文件和寫文章就夠我受的,更別提要那麼早起床。要是我願意早起,當初就不會離開——”
他停住話頭,顯然有點不好意思。艾希莉不禁好奇起來。
“繼續說呀,”她說,“如果你願意早起,當初就不會離開農場,對不對?”
洛雷登做了個鬼臉,點點頭。“沒錯,”他說,“一段恐怖的日子,幸好後來離開了。好——”
“噢,噢,”艾希莉愉快地嘟囔,“這麼說你真的是農家少年,對吧?老實說,我完全沒猜到。我正準備打賭說你一輩子都沒出過城呢。”
洛雷登竭力保持麵無表情。“我也隻去過一兩次。”他說,“我父親在中邦有一個小農莊。當然,他隻是佃戶。我們換個話題吧。”
艾希莉聳聳肩,有點不快。“不想提就算了,”她說,“我隻是好奇,沒別的意思。”
洛雷登謹慎地倒滿杯子,然後一飲而盡,幾滴紅色的酒順著他的下巴淌下來。“行了,”他說,“題外話說夠了。如果你覺得我幹不了助理,那我還是去教課吧。”他歎了口氣,“要是能有一兩樣跟這可惡的行業不沾邊的選擇就好了。”他說,“問題是,別的我都不會。”
“開家酒館?”
“太辛苦。”他笑道,“再說我對怎麼經營酒館一竅不通。是不是經常有服過役的老兵從戰場下來,開起了酒館?”
“表麵上是這樣,實際上通常是他們的妻子和女兒在經營。”艾希莉笑了起來,“我叔叔不再跑船以後開了一段時間酒館。他經營得很好,隻不過後來覺得無聊,就賣了酒館賺了一筆,買了另一艘船。”
“你在暗示我嗎?我得告訴你,我不會遊泳。”
“我叔叔也不會。我的意思是,不要讓自己被一個職業束縛住,動彈不得。”
洛雷登搖搖頭。“太危險,”他說,“我得瘋了才會讓自己一輩子待在被水包圍的地方。”
艾希莉沒有聽他說話,她忙著偷聽坐在他們後麵那張桌子上的人。洛雷登皺起了眉頭,隨即也注意聽起來。
“別做得那麼明顯。”艾希莉不滿地低聲嗬斥,“太尷尬了。”
“你還說我?你就繼續聽吧,不知道他們在聊什麼有意思的話題。”
“事實上,他們的話題就是你。應該是剛從法院過來。”
“哦。”
“外邦人。”
“啊,原來如此。”
洛雷登伸長了脖子,想看清楚點。他看到一個瘦臉、高顴骨的瘦高個男子,以及一個看起來明顯和他是孿生的女子。同樣的麵部特征在她那裏就順眼多了。
“別傻了,”男人正說道,“如果他的劍沒斷,他要幹掉你看好的那家夥就像切烤肉一樣容易。我一輩子沒見過比這更僥幸的事。”
“文納德——”
“更別提那不公正的結局了。”男人繼續說道,“另一方明顯在各方麵都比他強,隻不過在戲弄他而已。如果不是這樣,他早就可以結束這場決鬥了。我說啊,誰讓他對一個老家夥起了同情心呢,活該!”
“文納德——”
“太神奇了,說真的,這把年紀了還在打。我的意思是,這一行競爭非常激烈,隻有最好最強的才能存活下來。該死,我就算把一隻手綁在背後也能打得比他好——”
“文納德,他就坐在你背後。”
男人一下子僵住了,好像一隻腳踏進了陷阱似的,一動也不敢動。洛雷登發現自己正盯著女孩的眼睛,連忙把目光轉開。
“糟糕,維特裏絲,你幹嗎不——”
“我一直想提醒你,白癡。你最好馬上道歉。”
“他可能沒聽到。”
“他當然聽到了。你叫得像驢那麼響。”
“我才沒有叫得——”
“好,如果你不去,就隻好我去。”
“維特裏絲!拜托,你想幹——”
女孩站起來,走到洛雷登的桌子前。艾希莉將臉埋在手掌裏,竭力忍住不笑出聲來,洛雷登則忽然發現自己的靴子尖格外迷人。
“打擾了。”
洛雷登抬起頭。“有事嗎?”他說。
女孩甜甜一笑。剛才還覺得整件事有那麼一點意思的洛雷登開始煩躁起來。麵對刻意的殷勤,他總是有點不耐煩。“我想替我的哥哥道個歉。”她說,“你知道,我們是外鄉人——”
“別放在心上。”洛雷登說,“再說,他也沒說錯。”他作勢轉身倒酒,但效果被空空如也的酒壺破壞了。女孩似乎並沒有注意到。外邦人,他想,同時向艾希莉遞了一個“救救我”的眼神,卻被對方直接無視了。
“他沒意識到自己這麼沒頭腦。”女孩繼續說道,“老實說,有時候我都替他感到羞恥。他做事總這樣。”
洛雷登勉強對她笑了笑,開始受不了她的口音了。“是嗎,”他說,“沒關係的。艾希莉,我們一會兒預約的是幾點?”
“什麼預約?”
“你知道的,就是到城裏另一頭去辦事的那個。”
艾希莉從鼻子裏輕輕哼了一聲,搖搖頭,“我沒聽說啊。”她忍笑忍得很艱難,好不容易才把話說完。
“至少他應該請你們喝一杯。”女孩一邊說一邊向她哥哥招招手,後者正躲在一個空的蘋果酒壺後麵,盡量裝作不存在。“文納德,”女孩叫道,“請他們喝一杯吧。”
文納德慢吞吞地站起來,暗暗發下商人中間最狠的誓言,決心以後再也不帶他妹妹出門了。在老家,她從來不敢這麼做。看來越快回去越好。他拖拖拉拉地走開,點了一大壺葡萄酒,然後很不情願地到她妹妹這裏來。
“你真是太客氣了。”艾希莉說,“坐下來一起喝一杯吧。”
洛雷登瞪著她,還試圖在桌子底下踢她的腳,結果她把腳挪開了。“是啊,請坐。”他笑了笑,用倉促之間能使出的最敵意的語氣說道,“我叫洛雷登,這是我的助理,艾希莉。”
女孩有點吃驚。“你的助理?”她重複道。
“是的。我是一名辯護律師,她是我的助理。”他意識到女孩大概把艾希莉當成他的妻子了。他衷心期盼這兩個人能一起走開。
“原來如此。”女孩一邊說一邊在他對麵坐下來,“我叫維特裏絲,這是我哥哥文納德。我們從島上來。”
“來這裏做生意?”
維特裏絲點點頭。“文納德帶我入行。”她說,“這是我第一次出國。我們的父親去世前將船和貨物平分給我們倆。我就說,也許我也該盡一份力。”
“真的嗎。”洛雷登盡量讓自己的語氣聽起來不感興趣。他做得棒極了。“我想你一定充分利用這段時間到處看了看吧。”
“哦,是的。”女孩興高采烈地回答道,“所以今天我們才會去法院啊。文納德說,到了佩裏美狄亞卻不去法院參觀簡直不可想象。”
“但願你看得開心。”洛雷登依然不冷不熱地說。女孩忽略言外之意的能力特別強,居然熱情洋溢地直點頭。
“真的很開心。”她說,“太刺激了。事實上,我們剛才就在爭論這個。你瞧,文納德自詡為萬事通,但我告訴他,我從一開始就知道你會贏。”
“你錯了,”他說,“正如他所說,不過僥幸而已。”
“真的嗎?”女孩很驚訝,“你肯定是在自謙吧?”
“那我需要自謙的地方太多了。”
維特裏絲沉思了一會兒,大笑起來。“你讓我太吃驚了。”她說,“我以為你能輕鬆贏下,但事情並非如此。”她猶豫了一下,繼續說道,“這麼說,另一方折斷了劍是純屬偶然嘍?”
洛雷登瞥到艾希莉的目光,她已經不再傻笑了。他決定繼續聊下去,讓她也吃點苦頭。
“純屬偶然。”他說,“不過,這種事時不時會發生。因為我們在法庭上用的劍,劍刃比普通的要薄。區別在於劍芯是如何回火以及如何與劍刃釺接在一起的。如果劍芯在釺接過程中受到過度煆燒的話,劍身就會出現薄弱點。一旦薄弱點受力,劍就斷了——對不起,我講得太技術化了。”
“我明白了。”維特裏絲說,“我問這個問題,是因為在那把劍折斷前一秒,我已經預感到它會斷了。很奇怪,不是嗎?”
洛雷登搖搖頭,“我剛才說過,這種事時有發生。你得學會去麵對它,正如你不得不學會麵對死亡一樣。”他戲劇化地補充了一句。艾希莉拋給他一個“快住口吧”的眼神,他假裝沒看見。
維特裏絲睜大了眼睛。“所有的訴訟案都是生死決鬥嗎?”她問道。
“除了遺囑案和離婚案,其他都是。嚴格說來,它們的司法管轄權和其他案子不同。不過,審訊的時候是在同樣的法庭,由同一群法官做出判決。這個傳統可以追溯到遺囑查驗和家庭事務在牧師自設法庭審理的年代。”
“你們不是不信神嗎?”維特裏絲反駁道。
“我們現在不信,但我們有過信神的年代。”
“原來如此。是你們強行取締,還是人們漸漸失去了信仰?”
洛雷登聳聳肩。“我想,二者皆有。”他說,“當宗教逐漸開始失去人心時,皇帝乘虛而入,一缺錢就沒收教會財產。照我看來,就算不缺錢,他們也一樣會這麼做。總之,沒了金銀和地產,當牧師又有什麼意義呢?於是整個教會體係就此終結。”
全程僵硬地坐在那裏一言不發的文納德,終於想出了終結這個尷尬局麵的辦法。“不好意思,”他說,“你剛才是不是在打鬥中受傷了?”
洛雷登點點頭。“沒什麼大不了的。”他說,“正如你所說的,我很幸運。”
“傷口不需要處理一下嗎?”文納德急切地問道。
他話音剛落,洛雷登發現傷口又開始流血了。洛雷登抬頭看了對方一眼,目光銳利。然後他點點頭。“你說得對,”他說,“恕我不能奉陪……”
女孩有點失望。“好吧,”她說,“很高興認識你。等我回到老家,一定會告訴大家,我和真正的佩裏美狄亞劍士一起喝過酒。”
洛雷登強忍尷尬地笑了。“當然,”他說,“一路平安。”
洛雷登和艾希莉離開後,文納德長出了一口氣。維特裏絲先發製人。
“都是你的錯。”她說,“我幾次想提醒你,你卻不聽。”
“我早該知道什麼都是我的錯。”她哥哥歎了口氣,“在你闖出更大的禍之前,我們趕緊消停了回旅館吧。你不準——”
“真奇怪,”維特裏絲打斷他的話,“我真的預先知道他會贏,不騙你。但是談了幾句之後,我發現他也隻是個普通人。”
“我不知道他是什麼樣的人。”文納德回答道,“但在你滔滔不絕的時候,我聽到他至少設法插了三句話。我說,這已經很了不起了。”
維特裏絲沒理他。“好了,”她說,“我們趕緊去餐具市場吧,你可以教我怎麼挑選銅器。你不是說今天有好多事要做嗎。”
亞曆克修斯從他的書上抬起頭。“怎麼樣?”他說。
“他贏了。”
教長微微點頭,合上書,將它放在誦經台書架的盡頭處。“沒什麼。”他說,“進來喝杯蘋果酒吧。”
聽到“蘋果酒”這幾個字,卡納迪微微撇了撇嘴。“我不這麼認為,”他回答道,“這件事有點詭異。”他坐在房間裏唯一一張毫無裝飾的椅子上,繼續說道,“結局出人意料,純粹是運氣。阿爾維斯幾乎將他玩弄於股掌之間,但接下來他的劍忽然斷了。”
“說明我們的防禦場是有效的。”教長回答道,“我隻希望我們沒有做得太明顯。”
卡納迪搖搖頭。“問題是,”他說,“我不認為這是我們幹的。或者至少說,”他揪著短胡茬兒補充道,“不僅僅是我們。我發誓我能感覺到另外一個印記——”
“哦,拜托,”亞曆克修斯打斷他的話,“你知道我在這方麵的看法。”
他的同僚皺起了眉頭。“隻是意見不同而已。”他承認,“我很肯定,除了我們布置的防禦場之外,我還察覺到了別的什麼。別再給我灌輸什麼無意識神秘主義,還有做事要講實際之類的,我的結論純粹來自我的觀察。我認為我們的防禦場的確起了作用,不過隻是讓他可以不停地躲避來自對手的攻擊,不論對方使出的是妙招還是臭招。讓阿爾維斯的劍折斷的,完全是另一種力量。”
亞曆克修斯點點頭。“嗯,當然。它作用在阿爾維斯身上,很可能影響巨大。”他思考了一會兒。“也許是有人對阿爾維斯下了咒?”他推測道。
“有可能。不過說是詛咒有點過了。我感覺影響是很輕微的。不是說那股力量很小,而是它被應用在微不足道的小事上。與猛地一擊相比,更像輕輕一推,不知你能不能理解我的意思。”
亞曆克修斯背靠著牆,凝視著天花板上的馬賽克壁畫。無意間,他開始數起了星星。“這種現象很不尋常。”他說,“如果那股力量如你描述的那樣強大無比,那它帶來的反作用力將非常可怕。誰會動用這樣的力量,僅僅是為了——用你的話說——‘輕輕一推’?如果要承受如此高階的反作用力,那我肯定會挾雷霆之勢,一下子將受害者拍倒。”
“這點我也想過。但假如這是一種天然的能力呢?”
亞曆克修斯眯起了眼睛。“一個無意識的舉動。”他沉吟道,“有可能,但我認為這種現象極其罕見。也許是之前的那個學生。”
卡納迪搖搖頭,“那你肯定早就注意到她了。你從來不會忽略這種力量。”
“可能隱藏得很深。”亞曆克修斯大膽猜測。他揉著小腿背,緩解發麻的感覺。他房間的床用來睡覺都很不舒服,用來當椅子坐更是一個草率的舉動。“不對,如果她本身有天賦的話,在我施錯咒的時候就可以直接阻止我。而且我進去的時候,應該能夠感應到她留下的一絲無法掩飾的惡意。我想我們可以將她排除掉。但是有一個天賦者在法庭現場,這是個很合理的推斷。我可以想象,人群中有人全力支持處於劣勢的一方,腦海裏出現劍斷了,處於劣勢的一方得救後歡欣鼓舞的畫麵。純粹出於本能——”
“很有可能。”卡納迪站起來,繞著圈子走了幾步,又坐下來。“如果是這樣的話,”他繼續說道,“情況不是更複雜了嗎?如果我們不得不再次回到你腦海裏的畫麵,誰知道我們去了以後會看到什麼?”
亞曆克修斯躺回床上,閉上眼睛試圖清空腦子。最重要的,是找回權衡輕重緩急的能力。“在失去判斷力之前,我們是否應該先將後果想清楚。最糟糕的情況——”
“就是詛咒直接反作用在你身上。”卡納迪急躁地打斷他的話,“給你本人以及受你牽連的同僚帶來天大的麻煩。佩裏美狄亞的教長死於自己的詛咒——”
“別人怎麼會知道死因?”亞曆克修斯反駁道。
“我親愛的同僚,健康狀況極佳、吃穿不愁的人不會無緣無故蜷縮著死去。”
“告訴他們我病了有一段時間了,是自然死亡。事實上,甚至可以算是解脫。”他睜開眼睛,“你真的認為會走到這一步嗎?”
“我親愛的同僚——”
亞曆克修斯坐起來,腳一挪,踏到地上,“我認為,該輪到我對你說實話了。卡納迪,我毫無頭緒。”
“亞曆克修斯,你是教長——”
“是的,我是。作為教長,我算是世界上最了解元理規律的人。我卻對它如何起作用都不知道。你也是。”在卡納迪開口之前,他補充道,“我們的知識加起來——注意,是加起來——也不過是確定它會起作用。我們兩個窮畢生精力,研究幾百年來數千名哲學家和學者的著作,也隻是確認它會起作用。我們的了解僅限於此。更別提如何控製這種力量了。”
“是的,但是——”
“現在,”亞曆克修斯繼續道,“有證據表明城裏出現了一個能夠控製這種力量的天賦者。而且,”他略帶一絲苦澀,“多半是憑本能行事,甚至可能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在做什麼。這還不夠,更雪上加霜的是,我施的一個詛咒居然脫離掌控滿城市亂跑,並且對我緊咬不放。”他狠狠地咬著指節,“你知道嗎,當初我們就該將研究方向限定於數學以及道德範疇,畢竟這本來就是應該研究的方向——”
“沒錯,奈何我們沒做到。至少,你沒做到。”
“你不是挺樂意介入的嗎。”
“行了,”卡納迪用手摩擦著臉,“說這些沒用。如果我們克服不了這個難題,還有誰有這個能力呢?”
亞曆克修斯歎了口氣,“你自己剛才也說了,我是佩裏美狄亞的教長,而你是城邦學院的掌院。我們上任的同時也等於放棄了向他人求援的權利。”
“天賦者。”卡納迪忽然說道,“也許他能幫忙撥亂反正。”
“我們剛剛不是一致認為,他多半還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所作所為嗎?再說,即使我們能說服他相信自己擁有特殊的能力,他也不見得就能按照我們的要求行事。”
“我們好像別無選擇。”
“你說得對。”亞曆克修斯跌坐下來,下巴磕在胸口,“但我們怎麼才能找到你口中的天賦者呢?我們不能在城市裏瞎逛直到奇跡發生啊。”
卡納迪思考了很長一段時間。“說實話,”他說,“我想不出還有什麼別的辦法。”
“但這樣可能要找好幾年。我又沒有——”
“我知道。”卡納迪說,“仔細想來,還有一個變數。你在假設這位天賦者是這裏的公民。萬一不是呢?萬一他是個外邦人,來這裏做生意,過一兩天就要離開呢?沒準兒他已經離開了。”
“沒有證據支持這個假設。”
“是嗎?問問你自己,如果他是公民,從一出生就住在這裏,我們之前為什麼沒有遇上類似的狀況?這是他第一次展示能力的可能性太小了。”
“有這個可能。”
“確實,但可能性很小。他的力量是如此強大,以至於一個下意識的願望都能實現——”
“那隻是我們的推斷。”
“再加上我的觀察,別忘了。我就在那裏,在法庭上。”
“你說得對。”亞曆克修斯痛苦地說,“那麼,說吧,你有什麼建議。”
卡納迪聳聳肩,“除了滿大街搜尋,我沒有別的主意。當然,這麼做並不能保證——”
“設個陷阱。”亞曆克修斯忽然說道,“不,不能說是陷阱。是誘餌。誘使他再次使用他的特殊能力,或者在無意識中讓他的能力暴露出來。”
“好主意。你打算怎麼做?”
亞曆克修斯吸了口氣,從鼻子呼出來。“我不知道。”他承認。
卡納迪身子前傾,雙手托著下巴,“一定有我們可以請教的人。”
“我要跟你說多少次——”
“一個專家,”卡納迪回道,“我們需要一個專家。在這座城市裏研究元理的有多少人?幾千人。這裏麵一定有人專門研究這個方向。術業有專攻嘛。”
“你是說,我們召開一個秘密會議,告訴大家我們惹上了大麻煩,問問有沒有人正好可以拿出解決方案。拜托,卡納迪。”
“我們當然要謹慎。我們可以發表一篇滿是漏洞的論文,看誰會跳出來和我們爭辯。”
“好吧。你知道這麼做需要多久時間?而且,萬一被你料中,天賦者是個外邦人,正準備離開這裏怎麼辦?我們根本沒有足夠的時間。”
“你的意思是,瞎猜?”
“有根有據的猜測也好,俘獲天賦者的陷阱也好,”亞曆克修斯的目光越過十指相搭的雙手盯著地板中央懸掛吊燈的環。“總比坐在這裏吵來吵去強。”他苦笑道,“太有意思了,不是嗎?我們本該是這方麵的高手。”
“我們確實是。”卡納迪沮喪地回道,“這正是我擔心的。”
(1)一碼約為零點九一米。
(2)一磅約為零點四五千克。
(3)古羅馬扭力投石機的一種,因為其投射石彈像野驢被追擊時踢起石塊,所以又被稱為野驢砲(onager)。
(4)他們在以母語交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