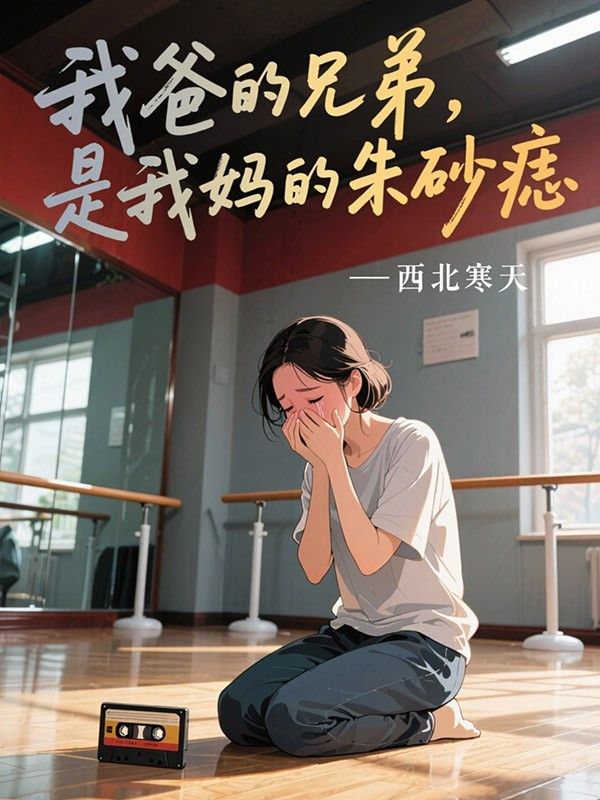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一章
我媽甘芷雪和我爸的鐵哥們付封墨,在我眼皮子底下曖昧了二十多年。
我爸褚星元明明什麼都知道,卻裝著一副好丈夫好兄弟的樣子,默默承受著綠帽子。
每次付叔叔來家喝酒,我媽都表現得特別周到。
她會提前問我爸:“阿墨今晚來?那我燉盅冰糖雪梨。”
酒桌上,她會給付叔叔盛湯,但話很少。
“阿墨,試試這個,我老家寄來的火腿。”
“最近胃還好嗎?聽星元說你又貪杯。”
我媽喊付叔叔,喊阿墨。喊我爸喊星元。
我質問我媽時,付叔叔那張溫潤如玉的臉上露出嘲諷:
“小丫頭,知道得太多可不是好事,你爸媽的婚姻需要你來指手畫腳嗎?”
1
這個周末,我們家又聚餐了。
我爸的鐵哥們,付封墨付叔叔,也來了。
他提著一個精致的紙袋,放在玄關。
“叔叔,你又買什麼好東西了?”
“沒什麼,出差路過,給你媽帶了盒她愛吃的桂花糕。”
我心裏“咯噔”一下。
那家老字號的桂花糕,隻在隔壁城市有店。
付叔叔的公司,明明就在本地。
飯桌上,我媽端出一碗湯,徑直放在付叔叔麵前。
“阿墨,特地給你燉的養胃湯,你嘗嘗。”
我爸在一旁夾著花生米,笑嗬嗬地說。
“你看看,阿墨的胃,現在比我的還金貴。”
空氣,在那一瞬間,好像凝固了。
我媽的笑容僵在嘴角。
付叔叔拿起勺子的手,也頓住了。
還是付叔叔先開了口。
“嫂子今天這個發型真好看,顯得特別有氣質。”
我媽的臉頰,騰地一下就紅了。
她下意識地攏了攏耳邊的碎發。
“哪有,老樣子了。”
我爸埋頭喝著酒,好像什麼都沒看見。
可我看見了。
飯後,付叔叔要走。
我媽站起來說:“我送送你。”
兩個人站在門口,壓低了聲音,不知道在說什麼。
我假裝去陽台收衣服,從窗戶的縫隙裏往下看。
付叔叔的車,在樓下那棵香樟樹下,停了很久。
久到煙頭的火星,在夜色裏明滅了兩次。
車才緩緩開走。
我爸洗完碗出來,擦著手問。
“跟阿墨聊什麼呢,那麼久?”
我媽正在收拾桌子,頭也沒抬。
“沒什麼,就是讓他開車慢點,注意身體。”
她的語氣,有點飄。
2
周二下午,我逃了課,去付叔叔的公司。
他說有個文化展需要人手,讓我去兼職賺點零花錢。
我幫著把一堆道具往倉庫裏搬。
經過他辦公室的時候,我的胳膊肘不小心撞到了書桌。
桌上的一個相框,“啪”地一聲掉在了地上。
我趕緊蹲下去撿。
相框裏的照片,滑了出來。
那不是什麼風景照,也不是什麼藝術照。
是我媽。
照片裏,我媽穿著一身練功服,在舞蹈室裏做了一個側影的動作。
光從窗外打進來,勾勒出她優美的輪廓。
那個拍攝角度,很近,很私人。
隨著相框倒下,一堆東西也從桌角的文件後麵散了出來。
是一本厚厚的攝影集。
我鬼使神差地,撿起來,翻開了第一頁。
我的呼吸,停住了。
照片上,是少女時期的我媽。
紮著兩個辮子,笑得一臉天真。
我繼續往後翻。
第二頁,第三頁,第四頁......
全是她。
穿著校服在圖書館看書的她。
穿著運動服在操場上跑步的她。
穿著長裙在舞台上領獎的她。
從少女,到青年,再到我熟悉的、現在的模樣。
每一張照片下麵,都有一行雋秀的鋼筆字。
標注著時間,地點。
甚至......
“一九九八年,夏。雪兒今天心情很好,因為舞蹈比賽拿了第一。”
“二零零五年,秋。她穿這件風衣真好看。”
“二零一六年,冬。她說她喜歡冬天的第一場雪。”
我的手,開始發抖。
“晚星?你怎麼在這兒?”
付叔叔的聲音,像一道驚雷,在我身後響起。
我猛地回頭,看見他站在門口,臉色慘白。
他快步走過來,一把奪過我手裏的攝影集。
動作快得,像是在撲滅一場大火。
他手忙腳亂地把照片和相框塞進抽屜裏,上了鎖。
“付叔叔......”
“這個......”他深吸一口氣,努力擠出一個笑容。
“這個是叔叔準備的,想在你媽生日的時候,給她一個驚喜。”
他的聲音,在抖。
我點點頭,假裝信了。
“哦,這樣啊,那我先出去了。”
我轉身走出辦公室,心臟跳得像要從嗓子眼裏蹦出來。
一個男人,為一個女人,做了二十多年的相冊。
這如果隻是“驚喜”。
那我就是個傻子。
3
我回家了。
像個幽靈一樣,在家裏飄來飄去。
我開始瘋狂地尋找證據。
我媽有個梳妝台,最下麵的那個抽屜,總是鎖著的。
她說裏麵放著一些貴重的首飾。
我趁她去洗澡的時候,用一根發夾,捅開了那把老舊的鎖。
抽屜裏沒有金銀珠寶。
隻有一個小小的絲絨盒子。
我打開盒子。
裏麵,是一條男士手鏈。
銀質的,款式很老,看得出有些年頭了。
但被人保養得很好,擦得鋥亮。
手鏈下麵,壓著一張小小的卡片。
上麵是熟悉的,付叔叔的字跡。
“雪兒,今晚的舞讓我想起了從前。”落款是墨。
日期,是上個月。
我媽她們文化館上個月確實有一場彙報演出。
我把東西原封不動地放回去,鎖好抽屜。
浴室的水聲,停了。
我媽裹著浴巾走出來,頭發濕漉漉的。
她看見我站在梳妝台前,眼神閃了一下。
“晚星,你在這幹嘛呢?”
“沒事,找個眉筆。”
她沒再說什麼,隻是走到梳妝台前,下意識地拉了一下那個上鎖的抽屜。
那個動作,暴露了她的心虛。
晚上吃飯。
氣氛詭異得能結出冰。
我跟我媽,兩個人,都在演戲。
她假裝什麼都沒發生。
我假裝什麼都不知道。
突然,她給我夾了一筷子菜。
“今天去阿墨那裏,感覺怎麼樣?”
她的語氣,很隨意。
但她的眼睛,死死地盯著我。
像是在審問一個犯人。
我低下頭,扒拉著碗裏的飯。
“挺好的,付叔叔對我特別照顧。”
我能感覺到,她那道緊繃的視線,瞬間鬆弛了下來。
她長長地,舒了一口氣。
4
付叔叔又來家裏吃飯了。
這次,我不再是那個懵懂的觀眾。
我變成了一個拿著放大鏡的偵探。
我媽給付叔叔盛湯。
碗遞過去的時候,她的指尖,輕輕地,碰了一下他的手背。
一觸即分。
快得像個錯覺。
但我爸,剛好抬起了頭。
他看見了。
他的眼神,暗了一下。
隨即,他又若無其事地低下頭,繼續喝酒。
飯桌上,付叔叔說起最近公司壓力大,總是失眠。
我媽立刻接話。
“那胃藥還夠嗎?要不要我再去給你買一點?”
這句話,信息量太大了。
證明他們平時,一直有聯係。
我爸夾菜的筷子,停在了半空中。
但他很快就恢複了正常,甚至還笑了笑。
“雪姐就是心細,比我這個當哥們的還關心阿墨。”
他喊我媽“雪姐”。
一個奇怪的,帶著疏離感的稱呼。
吃完飯,我爸主動站起來。
“你們聊,我來收拾碗筷。”
他把空間,留給了我媽和付叔叔。
這種“善解人意”,讓我覺得毛骨悚然。
我跟著進了廚房。
“爸。”
“嗯?”
“你不介意,我媽跟付叔叔走得這麼近嗎?”
我把問題,像一把刀子,捅了過去。
他洗碗的動作,停頓了足足有五秒鐘。
然後,他重新打開水龍頭。
水聲嘩嘩作響。
“老朋友了,幾十年了,應該的。”
他手裏的那隻青花瓷碗,被他搓得“咯吱”作響。
我真怕他下一秒,會把碗捏碎。
5
周末,我爸帶我去釣魚。
就我們兩個人。
我找了個機會,狀似無意地問。
“爸,你當年是怎麼追到我媽的?聽說她當時可是我們學校的校花。”
我爸的臉上,露出了得意的神色。
“那可不,你媽當時可搶手了,追她的男生,能從東門排到西門。”
他的話匣子,打開了。
但當他說到付叔叔的時候,語氣,明顯變了。
“阿墨......阿墨那時候,也挺喜歡你媽的。”
“他們是舞蹈社的搭檔,還一起上台跳過舞,配合得特別好。”
我追問:“那為什麼最後是你成功了?”
我爸沉默了。
魚竿上的浮漂動了一下,他猛地一拉,一條小鯽魚被甩了上來。
他一邊取鉤,一邊含糊地說。
“可能......可能是我臉皮比較厚,比較有誠意吧。”
他把魚扔進桶裏,又說了一句。
“有時候,你媽晚上做夢,會說胡話,叫一些......奇怪的名字。”
我的心,沉到了穀底。
他又給自己點了根煙,眼神飄向遠處的水麵。
“阿墨這個人,重感情。這些年,一直沒結婚,我有時候覺得......挺對不起他的。”
這句話,像一聲驚雷,在我腦子裏炸開。
我爸,他什麼都知道。
他不是遲鈍。
他是在裝傻。
6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半夜,我聽見我媽的房間裏,隱隱約約傳來音樂聲。
是一首很老的情歌。
我悄悄地爬起來,走到她房門口。
門,虛掩著一條縫。
我湊過去,從門縫裏往裏看。
我媽沒有睡覺。
她坐在地毯上,背對著我,正在看一盤錄像帶。
電視屏幕的光,照亮了她半邊臉。
畫麵裏,是年輕時的她,和一個同樣年輕的男人。
那個男人,是付叔叔。
他們在舞台上,跳著一支雙人舞。
配合得天衣無縫。
眼神纏綿。
愛意,幾乎要從屏幕裏溢出來。
我媽伸出手,輕輕地,撫摸著屏幕上付叔叔的臉。
她的肩膀,在微微地顫抖。
我聽見了,壓抑的,小聲的啜泣。
錄像帶播到了最後。
音樂停止,兩個人擺出了結束的造型。
他們的臉,離得很近很近。
近到,幾乎要吻在一起。
就在那一刻,我媽按下了暫停鍵。
整個房間,都安靜了下來。
她就那麼靜靜地坐著,看著那個定格的畫麵,看了很久很久。
然後,我聽到她用一種近乎於夢囈的聲音,說。
“阿墨......我們,回不去了。”
我的心臟,像是被人狠狠地攥住。
疼得我無法呼吸。
7
我感冒了,發燒,一整天都躺在床上。
我爸出差了,要三天後才回來。
下午,我睡得迷迷糊糊,聽見了門鈴聲。
是我媽去開的門。
然後,我聽到了付叔叔的聲音。
他不知道我在家。
我躲在臥室裏,豎起耳朵,聽著客廳裏的動靜。
他們的聲音很輕,很溫柔。
像是在說什麼悄悄話。
我悄悄地把門打開一道縫。
客廳裏,付叔叔坐在沙發上。
我媽,就坐在他旁邊。
他伸出手,握住了我媽的手。
我媽沒有掙脫。
“星元出差了?”付叔叔問。
“嗯,要三天才回來。”我媽的聲音,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放鬆。
“我想你了,雪兒。”
付叔叔的聲音,沙啞,又深情。
我媽的眼睛,一下子就紅了。
“我也是。”
我看到,付叔叔的身體,慢慢地,慢慢地,向我媽靠近。
我媽也微微地,向他傾斜。
他們就要抱在一起了。
就在那個瞬間,我喉嚨一癢,忍不住,重重地咳嗽了一聲。
“咳咳!”
客廳裏的兩個人,像被施了定身法,瞬間僵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