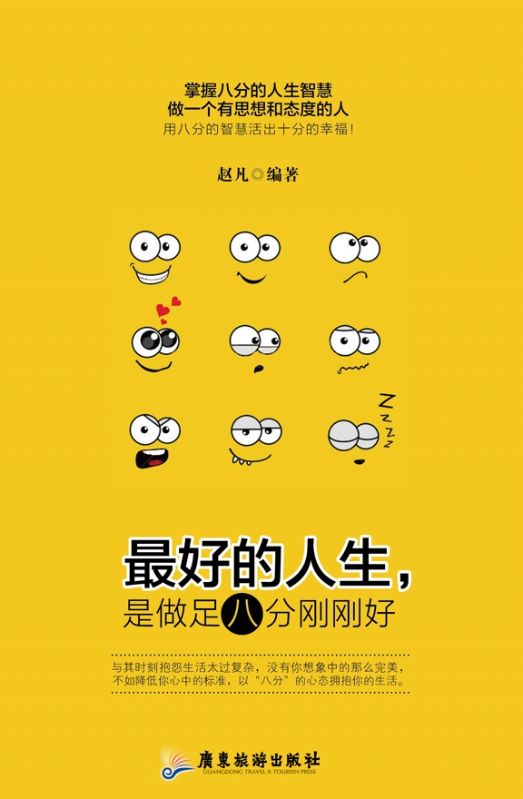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生命的價值在於什麼
生命的價值在於探索。因此,生命的唯一養料就是冒險。
一個孩子到一座廢棄的樓房裏玩耍,聽見一陣陣悲傷的哭泣聲傳來。孩子尋聲找去,在一個角落裏,有一個四四方方的鐵籠,裏麵囚著一個瘦得皮包骨頭的人,哭泣聲就是他發出來的。“你是誰?”孩子問。“我是我的生命。”那人說。“誰把你關在這裏的?”孩子問。“我的主人。”“誰是你的主人?”“我就是我的主人。”“嗯?”孩子不明白了。“我是自己把自己囚禁起來了。當我歡笑著企圖在人世間展示我生命的歡樂時,我發現我有可能一不小心落入陷阱,一不小心誤入黑暗之中,一不小心被狂風暴雨襲擊、被險風惡浪吞噬,於是我用害怕做經,用懦弱作緯,用安全做成鐵籠,把我的生命囚禁了起來。我不敢也無法衝出鐵籠去麵對生活,我隻有日複一日地哭泣,我的整個生命已經化作淚水流出,不久就會幹枯了。”鐵籠中的生命說。孩子不明白他嘮嘮叨叨地說些什麼,隻是想著:砸碎這鐵籠,放出這個快要幹枯而死的生命。於是他找來一把大榔頭,拚足力氣,向鐵籠砸去,一下,兩下,三下……孩子累得精疲力竭,也無法砸開鐵籠。被囚的生命對孩子頓生憐憫之心:“唉,把榔頭給我,讓我自己砸開它吧。”話音未落,鐵籠頓時散開。被自己放開的生命歡笑著,奔跑著,他跳進滾滾大河,遊向對岸;他攀向巍巍峰頂,向太陽招手;他衝進一片黑暗領地,從中尋求著光明……他敢於冒別人沒冒過的險,敢於探索別人不曾涉入的領地,他開始豐潤了、充實了,他的笑聲無時無刻不在追隨著他。
一天,孩子又遇見了這個生機勃勃的生命,“你的變化好大呀!”孩子說。
“是呀!”這個生命說,“我的樂趣就在於探索和冒險,當我在充滿未知和危險的世間尋求時,我就變成了現在這樣,假如我企圖尋求一個生命的保險箱時,我就會再次被囚。孩子,跟我一起走吧!”於是孩子和這個歡笑著的生命手拉手地走了。
我們追溯著命運,在物質中,在心靈中,在道德中,在種族中,在階級中,同樣,也在思想和性格之中。無論在哪裏,它都是束縛與局限。然而命運自己也有主人,局限性本身也有局限。從上觀察和從下觀察,從裏觀察和從外觀察,它們自身也不盡相同。這是因為,盡管命運是無窮無盡的,可力量也是無窮無盡的。如果說命運緊逼著力量、限製著力量,那麼力量也伴隨著命運,反抗著命運。我們必須尊崇命運為自然的曆史,可是曆史決不僅僅限於自然的曆史。
如果我們生活得真實,那麼在我們眼中顯現的也隻有真實,那就像強者永遠堅強,而弱者隻能軟弱一樣。現在的人越來越膽小怕事,整天一副內疚的樣子,好像犯下了什麼滔天大罪似的。剛強的氣質已經棄他而去了,他再也不敢說“我認為”“我就是”這些擲地有聲的語言了,而隻會引經據典,用自己的嘴巴去說別人的語言。麵對著一片草葉或一朵盛開的玫瑰花,他也氣餒萬分,無地自容。
然而,有人卻總是生活在過去,他牢固地把持著記憶,不肯放鬆,哪怕是很短的一會兒工夫,所以,他不是生活在現在,而是眼睛向後,在為過去而傷懷不已;要麼,他就對周圍的財富置之不理,卻使勁地踮起腳尖,對未來的日子想入非非。我們必須警告他,如果他不跟大自然一起超越時間,從現在開始生活,那麼,他永遠也不會快樂,也永遠不會堅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