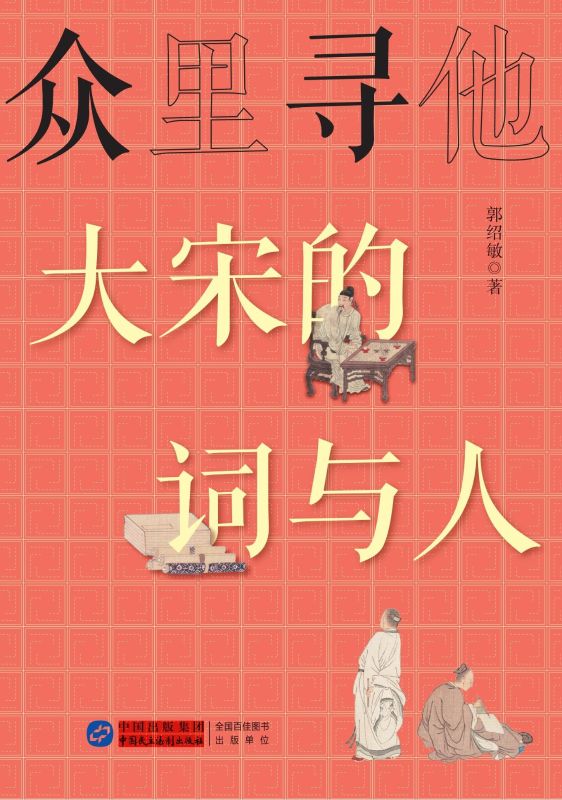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7.四月十七
總有些日子,我們無法忘記。比如說國慶日,結婚日,自己、愛人和孩子的生日,或其他具有特殊意義的日子。韋莊的《女冠子二首·其一》曰:
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別君時。
忍淚佯低麵,含羞半斂眉。
不知魂已斷,空有夢相隨。
除卻天邊月,沒人知。
韋莊念念不忘的“四月十七”,是他上一年和戀人離別的日子。而我念念不忘的是“七月十四”——2001年7月14日。那時,我剛剛大學畢業,即將進入研究院攻讀碩士學位。一個有點波斯人氣質的溫婉女孩坐火車來看我。我們是初中同學,她因家庭原因轉學到洛陽,後來考到南方一個離家很遠的城市讀大學。我們中間好幾年未見,但經常通信(指書信,那時手機屬於奢侈品,我們窮學生用不起),在信中討論林徽因、海子、《傲慢與偏見》、足球、劉德華、張曼玉、懷素、舒伯特、杜尚、熵、性、薛定諤、愛因斯坦……總之無話不談。我們像有默契似的,一直不見麵,也不說“Love”,覺得那樣才夠浪漫。2001年7月14日,她沒提前打招呼,就突然來看我了。我欣喜、激動,又有點不知所措。吃完晚飯,我們在大街上漫無目的地閑逛,快淩晨十二點了都沒有分別的意思。路上幾無行人,天邊的月亮默默地跟著我們走。我們走,月亮走;月亮走,我們走。終於,我們在學校附近的小賓館開了房,擁抱在一起。她“含羞半斂眉”“半羞還半喜”,而我緊張得要命,手忙腳亂地愛了一夜,卻並沒有越過最後的雷池。非她不願,實在是我的身體不配合(緊張所致),無能闖入禁地。隻差臨門一腳,現在想來有點丟人,也有點遺憾。暢銷書作家傳授經驗時說道,小說中的女主角不到最後不可失身。她那晚沒有失身,翌晨離開時也“欲去又依依”,我們的故事卻並沒有下一章,更沒有最後一章。魂已斷,空有夢相隨。現在智能手機早已普及,大學生不再寫信了,而我,偶爾把以前的書信偷偷翻出來瞅一瞅(“咫尺畫堂深似海,憶來惟把舊書看”),無限惆悵。不知她惆悵否?
無法忘記7月14日,還有一個“高大上”的理由:它是法蘭西共和國國慶日。1789年7月14日,巴黎群眾攻占巴士底獄。
我好讀史,且對法蘭西文學情有獨鐘。
那藍白紅三色旗,那茶花女,那梅裏美、比才和卡門,那在法蘭西勤工儉學的領袖,永遠引領我們飛升。若茶花女到中國來,韋莊請她喝紹興花雕酒;若卡門來,我請他喝北京二鍋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