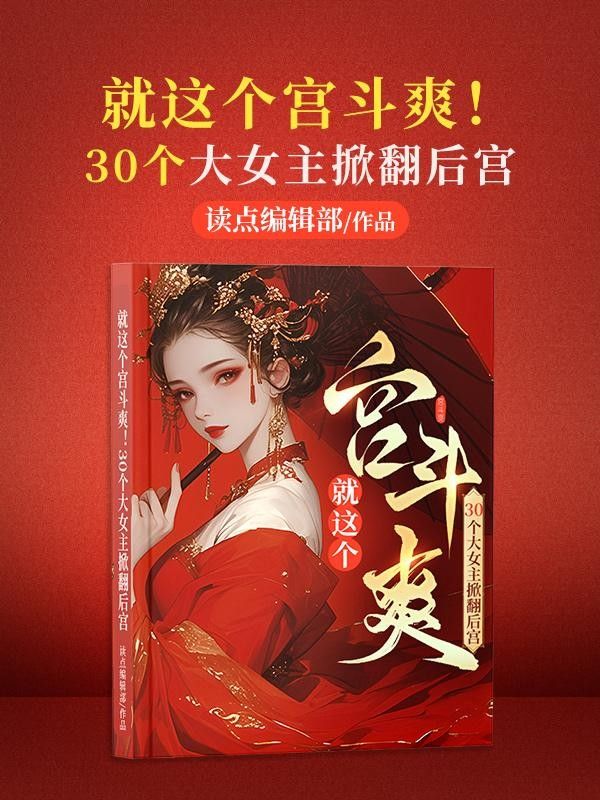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15章
東宮美人(五)
夜裏宮人來信稱今夜陛下歇在棋玉殿中。
我低歎,白日的落水風波,陛下隻挑阿詢的錯,棋玉摑他那一巴掌卻絕口不提,連一句申斥都沒有。
我與蕭禮多年夫妻,早在生產那夜就對他徹底寒心。
但阿詢一個六歲孩童,怎麼會不委屈?我帶了宵夜去看阿詢時,這孩子已經抄起《孝經》來了。
見我來,他未說話,眼中卻浮起水霧。我如何能不心疼,「吃些東西吧,明日再抄。」
他低著頭,說:「母後,是詢兒不好,不得父皇歡心。」
我撫上他的肩頭,心中酸澀難當,向他解釋緣由:
「你是母後最心愛的孩子,你很好。至於你父皇,他喜愛德妃多於我,自然就更喜歡德妃所生的阿囂。
「何況你與阿囂不同,你是中宮嫡出,你的成長就意味著你父皇的老去。
「他忌憚你,便不能全心意的愛你。但你還有母後。」
宮裏的孩子大多早熟,那一夜,蕭詢沉默著抄完了百遍《孝經》。
天光大亮時,他終於停筆,向我輕聲說:「母後,我知道的,其實您也喜歡並蒂蓮花。」
他提起並蒂蓮,恍然間,我想起了當年宮裏賞下來的蓮花釵來。
我是在生下樂溫後的第二年,一個偶然的契機,從太後口中方知道自己是如何成為東宮太子妃的。
太後說,當蕭禮向他們相求之後,岑家暗中就進了帝後的人,以考察棋玉的品德。
棋玉鬢發上的兩支蓮花釵太過紮眼,陛下覺得棋玉過於貪婪,不夠謙遜,故而改了人選。
如果這話是在我未出閣的時候聽到,或許會信,但現在我已浸潤宮廷數年,不由哂笑。
京都貴女那麼多,即使不選棋玉,何必將自己推上來?
歸根結底,太上皇是覺得蕭禮在婚姻一事上過於放肆,有意敲打罷了。
畢竟,國朝此前也不是沒有被廢的太子妃,若我真的不行,廢了,再換一個便是了。
待蕭詢睡下後,我命窈絮回了趟家。
窈絮是家生子,父母都是府中的老人,又沒兒子,本是要作為陪房隨我出嫁,我既嫁入宮中,他們一家便留在府裏。
又過了幾日,阿詢就帶著妹妹出宮去了,他們去了太上皇與太後養老的長壽莊。
那裏有的是空地,樂溫的美人風箏可隨意放飛而不必擔心被什麼勾住而敗了興致。
6
宮中時日如流水,神鳳七年的時候,太上皇薨。
眾多子孫中,最傷心的要數阿詢。他常去長壽莊走動,與太上皇祖孫情篤。
我擔心他的身體,燉了好些補身的湯水。
而太上皇出殯那日,當著眾多朝臣和宗室的麵,站在最前麵的阿詢忽然噴出一口血來,身子猛烈一晃,隨即摔倒在地昏迷不醒。
太醫診斷出此乃中毒所致。
蕭禮自然是震怒的,一番查證之後,凶手指向了賢妃蘇氏。
阿詢所中之毒乃是西南奇毒,而偏偏賢妃之兄多年以前曾經鎮壓過西南蠻兵。
況且在嚴審之下,我殿內已有宮婢招認,受了蘇家的恩惠,將毒藥溶在水裏,又以蘸過毒水的布帕擦拭了底下人替蕭詢整治膳食時所使的湯煲。
一夕之間蘇家倒台,連帶著賢妃所生的皇三子都受了厭棄。
這場雷霆之怒砸到蘇家頭上時,棋玉正臥床休養。
歲月似乎格外偏愛她,不肯讓她的美麗有半點損耗,即使小產之後麵容蒼白,瞧著都有病西施的美態。
她這幾年懷了兩次孕,每一次都沒有保住,最初也疑心我或者賢妃做了手腳,可她的近身之物一向小心,怕還是天生體弱之由。
神鳳十年的時候,我生了一場重病,久也不見好。
蕭禮漸信道教,要我上章首過,被我斷然拒絕:「為太子妃、為皇後,我問心無愧,並無過錯。」
真是這樣嗎?隻有我自己知道,真相如何。
我嫁給蕭禮十七年來,的確做過不少壞事。
譬如說,我從娘家入手,在母親的衣料和岑家獻給棋玉的溫補藥材上動了手腳,無聲息地弄掉了棋玉的子嗣。
可重來一次,我還是會這麼做,我與棋玉各有子嗣,勢同水火,我不能給她任何踩在自己頭上的機會。
在一雙兒女的陪伴下,我最終從這場疾病中挺了過來。
病愈後不久,請陛下立嫡長子蕭詢的折子便飛到了陛下案上。
從禮法上來說,蕭詢的繼立名正言順,但蕭禮卻按下不發。
他不想冊立太子又怎樣,他拖不了幾天了。
因為——
陛下千秋節那日,在宮廷宴會中,平日裏甚少出麵的皇二子列席。
到他獻壽時,皇二子卻替他的母妃喊起了冤。
當塵封已久的人名被翻了出來,陛下一霎怔愣後,記憶裏浮現出賢妃的臉來。
地上跪著的皇二子形銷骨立,死死地睜大眼睛瞧著自己。
賢妃是因長子蕭詢中毒一事才打入冷宮,若是賢妃有冤,那麼……
高高在上的帝王眼中閃過一絲莫名狂熱:「你先起來,你說賢妃有冤,可有什麼證據?」
我垂下眼睫,輕輕吹了吹杯盞中的熱茶。證據,自然是有的。
在陛下的授意下,賢妃之案重審。但所謂真相卻並不肯像他預料想的那樣。
當年被處決了的宮婢原來留有家人,十來歲的小姑娘跪在地上哀哀哭泣著,說著她知道的真相:
「母親告訴我,姐姐入宮後開始時在禦花園裏侍弄花草,有一年母親生了病,姐姐在禦花園裏哭,遇見了德妃娘娘。
「德妃給了我姐姐銀錢,要她將錢帶出去給母親治病。後來姐姐因著機緣入了皇後宮裏,德妃便要姐姐充當眼線……
「後來父親喝醉酒,打死了人,要償命。姐姐又求到德妃那裏去。
「德妃說,可以幫這個忙,但卻要姐姐日後為她做一件事。這件事,便是給太子下毒,同時攀咬賢妃……」
夠了,戲唱到這裏足矣。
我冷聲道:「好個德妃!好個一石二鳥的毒計,要不是當年阿詢喝得少,今天陛下身邊可用的豈不是隻剩下由她所出的阿囂!」
當證據攤到明麵上時,同當年的賢妃一樣,棋玉亦不住喊冤。
可若喊冤有用,賢妃便不必在冷宮裏磋磨了三年。
賢妃被釋出,三年冷宮生涯,將她折磨的如同老婦一般。就算出來了,帝王的寵愛也與她無緣。
棋玉則被送到城郊廟裏,青燈古佛,了此一生。
她出宮前,我們姐妹見了一麵。
棋玉已不再是當年不諳世事的愚鈍少女,她指著我,目眥欲裂:「是你,是你三年前就開始布局來害我!」
我輕輕搖頭:「棋玉,你大錯鑄成,卻還不知悔改,隻願青燈木魚,能讓你懺悔自己的罪過。」
這也是我今生,與她說的最後一句話。
多年前她曾給我上過一課,人越是得意,就越要警醒。
後來窈絮告訴我母親求見的消息。
我替女兒剝著龍眼,道:「告訴母親,陛下將棋玉送至廟裏已是網開一麵,賢妃卻在冷宮裏熬了三年。廟裏縱然清苦,總比冷宮裏強。」
一月後,陛下立嫡長子蕭詢為太子。
阿詢身份貴重,更何況,除阿詢以外,他已沒得選。
事情到這,便隻剩下熬時間了。
就像陛下昔日在東宮裏做的一樣,熬到皇帝肯退位,或者熬到皇帝駕崩,便算是熬出頭了。
我唯一擔心的是那來自西南的毒藥在阿詢體內還有殘留——三年前,兒子拿著毒藥找到我時,我著實吃了一驚。
但這步棋,雖然耗時長些,但的確奏效。
棋玉的冤並沒有喊錯,可冷宮裏的賢妃和三皇子都認定了凶手是她,死去的宮婢家眷也認定了是她,就算有一百張口,事也說不清楚了。
畢竟誰也想不到,這樣凶險的毒,竟然是十三歲的阿詢掐算著劑量,自己服下的。
比起他昔日的父皇來,蕭詢更適合當一個太子,他受到的帝王猜忌更多,應對的也更加周全。
在更漏聲聲裏,我沉沉閉上雙眼。
睡前想著,該找個時機要向陛下進言,後宮空虛,應廣選美人。
如今民富國強,一位天子稍稍放縱享受,是無可厚非的事情。
若皇帝不昏庸,如何顯出太子的賢能來。
半夢半醒中,我似乎又回到了年少時的歲月。
那時的我絕想不到有朝一日將在深宮裏,與姐妹相鬥,與帝王相鬥,機關算盡,詭計百出。
或許,這就是深宮內,所有女人的命運。
暗夜裏,不知哪裏響起淙淙琴聲來,如泣如訴,不絕如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