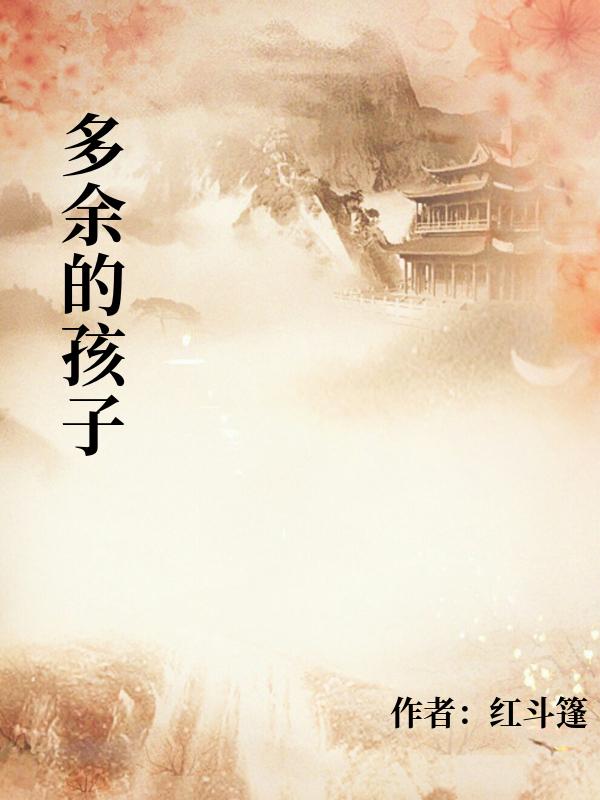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一章
我是家裏多餘的人,爸媽生我隻是希望我能照顧自閉哥哥。
在哥哥為救我溺水去世後,爸媽把我的衣服被扔出家門,說:「滾啊,為什麼死的不是你?」
我隻好將手中的病曆塞進口袋,離開了這個城市。
三個月後,收到我死亡通知的爸媽崩潰了。
我實在不知如何坦白自己快死了這件事。望著病曆上的「腦癌晚期」的幾個大字,我隻覺得這一生真是可悲。
我是為哥哥出生的。他患有先天自閉症,雖然經過積極治療已經有了很大改善,但爸媽始終放心不下,為了寶貝兒子老有所依才又生了我。
當然,這也成了他們這一生最後悔的決定——他們的寶貝兒子,因為救我,死了。
出事那晚天上天很冷,我像缺水的魚一樣躺在岸上,濕漉漉的身體顫抖個不停。
忽地,有人把我拽了起來,給了我一巴掌。很重的耳鳴後,各種聲音混在一起,其中最清晰的是我媽的哭嚎和我爸的責罵。
其實不光爸媽責罵,我想的也是如果沉下去的是我就好了。
可現下的局麵卻是我沒死成,但終是要死的。醫生說,如果我積極治療的話,大概還能活個一年到兩年。
「你害死了你哥!」
「你個討債鬼,因為你我們家破人亡!」
夜裏驚醒,我頭痛欲裂,遍體生寒。
爸媽說得沒錯,我無力反駁以上罪名。
很長一段時間,我都瘋狂嫉恨著我哥——從我六歲就被要求獨立上下學開始。
「哥哥還十歲了呢,為什麼他就有人送?」
小小的我深感不公,為此哭鬧不止過,我媽哄了我幾句不見效後,一把將我從地上揪起來,掐著我屁股上的軟肉罵:「哥哥生病了你天天還比來比去,小小年紀怎麼可以這麼自私?」
這是「自私」這個詞第一次貼我腦門上,我又羞又惱,卻反駁不出任何,隻隱隱恨上一旁早已嚇呆的哥哥。
我小學四年級時,爸媽怕比同齡人小兩屆的哥哥受欺負,把他送去了一學期幾萬的私立中學。
但相應的,家裏開支減少,一家子過得捉襟見肘。
倆孩子都正是嘴饞的年紀。當媽媽把湯裏唯一一個豬蹄尖夾給了哥哥時,哥哥看了看豬蹄尖,又看了看一旁眼巴巴的我,最終萬分不舍地把豬蹄一點點往我這邊推。
媽媽拿筷子摁住了哥哥,說教道:「女孩子吃豬蹄尖會把福氣叉走,給你的你吃就是了,她多喝湯也是一樣的。」
這世上總有那麼多針對女孩的規矩,我恨這個世界,也恨被世界偏愛的哥哥。
然而,我最恨的是他的十六歲。
那年,媽媽不知從哪掏出大師開過光的玉,獻寶一樣地招呼他戴上:「過來頌祺——戴上平安玉,以後都平平安安好不好。」
哥哥小心地摩挲著平安玉,看得出他很珍惜。這母子和睦的一幕讓我很是羨慕,我抱著一絲期待,期期艾艾道:「我、我也很喜歡,有我的嗎媽媽?」
媽媽臉上有些掛不住,不耐道:「下次吧,下一次看到好玩的給你帶。」
我清醒過來,不再指望任何。然而晚飯前,這枚平安玉還是到了我手裏——
哥哥借喊我吃飯的空隙悄悄把它塞給了我。
我迷茫了:「為什麼你什麼都願意給?」
哥哥一臉天真:「因為妹妹喜歡。」
他的大度也讓我嫉妒。
我不願讓自己太狼狽,所以動作凶狠地扯著他的衣袖說:「你拿走,誰要你假惺惺的了!」
哥哥不願收,隻背著手像做錯事的小孩。
僵持太久誤了飯點,媽媽進來一看我倆都紅著眼,便反手給了我一巴掌:「膽子肥了敢欺負哥哥,都說了下次給你買了,怎麼還不依不饒?」
臉上一片火辣辣地疼,我捂著臉,顫聲問:「媽媽,能不能對我公平一點......如果你隻喜歡哥哥,當初又為什麼要生我?」
毫無意外的,揪著我的領子把我丟了出去。我媽關門之前罵道:「你這個樣子也配人喜歡麼?養你還養出孽來了,怨氣這麼重就給我滾出去。」
十二歲的我是個連身份證都沒辦的小破孩,出了家門根本就無處可去。看著夜幕一點點黑下來,我終是害怕了,哭著拍門認錯。
這天後,一切回到正軌。我也當無事發生,來掩飾心裏的絕望和嫉妒。
哥哥自從戴上平安玉後,雖然成績依然不好,手工卻漸漸出挑,走藝考去了不錯的大學。
這下哥哥成了父母最成功的作品,他們將全部的期望寄托在了哥哥身上。我也以為,哥哥會長成手藝人的。然而,這一切的一切,都終止在那個可怕的夜晚。
千不該萬不該,那天晚上我不該與家裏吵架,不該完架後逃也似的跑出來。
可當時的我難以控製自己的情緒——我爸媽為了一點蠅頭小利,竟然打算把我嫁給一個比我大十幾歲的中年人。
我媽苦口婆心道:「女孩子花期短,反正你這點分數也上不了什麼好大學,不如早點把婚事定下來,也讓家裏安心一些,你說是吧,孩子他爸?」
我爸被點名,再無法裝聾作啞,忙跟著附和說我不要挑三揀四,等熬成老丫頭就不值錢了。
原來我在他們眼裏,隻是一樣待價而沽的商品,他們怕錯過了時令,所以急著把我售出。
我忍著眼淚問:「你們也會拿哥哥換錢嗎?」
我媽重重擱下筷子:「陰陽怪氣什麼,男孩女孩不一樣,你到底想和哥哥比什麼?」
這個回答真是糟透了。
我跑了,一個人走在街頭淚流不止。等走不動了,便坐在路邊長椅上發呆。
風一過,我瑟瑟發抖。
肩頭忽地有件外套蓋下來。我回頭看見了本該在外地讀大學的哥哥。
顯然,他逃了課。我問他為什麼在這裏,他卻隻說:「回家去吧,爸媽都在找你......」
他嘴笨,隻會反複地說同樣的話。我聽著他的念叨,心裏的厭煩升騰而起——他一個幸運兒,不過是站著說話不腰疼罷了。
我打斷道:「我討厭你!這輩子當你的妹妹,我真是倒了大黴。」
與我的刻薄相反,哥哥隻低下頭,輕輕嗯了一聲,一副逆來順受的模樣。
我忽然有些不是滋味。
其實這些年,他對我這個妹妹不差。媽媽偷偷給他加的餐,爸爸暗地塞他的零用錢,有不少他都私下塞我口袋了。
就像現在,他風塵仆仆,臉上還有細汗,卻顧不得休息,在我身邊坐下後,不僅把脫下的大衣披給我,還把五年前我就覬覦的平安玉掛在我脖子上,完了還不許我摘下來。
我不知如何理處理這複雜的恩怨,於是更恨他了,巴不得這輩子都和他脫離關係。
最終,我下定了決心,說:「哥,去幫我買瓶水吧。」
這是我這麼多年,第一次叫他哥。他受寵若驚,立刻站起身說:「好,你等我。」
我沒有回答他,等他走遠後,獨自走向河流。
渾濁的河水一點點浸濕褲腳,刺骨冷意蔓延我的全身。我是真的厭倦,這無休止的落差。我不準備逆來順受了,我要徹徹底底地逃離。
但我沒想到,我的逃離不僅失敗了,還害了哥哥。
我的傻哥哥,竟折返回來跳進河裏,拚盡力氣推對他滿心怨恨的妹妹上岸。
我有時也會忍不住想,如果那天,我沒有進到河裏的話,會如何呢?
可惜世間沒有如果。
那天像一場噩夢,我的父母失去了他們最愛的兒子,而我也失去了這個家唯一愛我的人。
哥哥去世後,媽媽失去了精神支柱,成了日夜翻看相冊流淚的婦人。
我也試著道過歉,但隻要我發出聲音,都會引來我媽的崩潰。現在的她厭惡一切動靜,包括滾筒洗衣機的轟鳴、枝頭鳥兒嘰嘰喳喳的鳥叫......當然,她最厭惡的是我。
媽媽說,是我害死了哥哥。
她將僅剩的一個台燈也被砸向窗戶,碎片飛濺,窗玻璃裂開了一個大口。
一地狼藉裏,我媽哭嚎不止,我爸為防她傷人傷己緊緊抱住了她。
幾個小時後,媽媽終於脫力睡下,同樣精疲力盡的爸爸路過我的房門,對坐在床上發呆的我冷聲說:「滿意了嗎?」
聽到爸爸的話,我錯愕地抬起頭,幾乎要呼吸不上來。
他繼續道:「你從小就嫉妒你哥,現在哥哥走了,家也散了,你應該很開心吧?」
我以為我爸這麼多年的沉默隻是不善言辭,沒想到,我在他眼裏竟是如此的卑劣不堪。
開心嗎?應該開心嗎?
我捂著疼痛不已的胸口,感覺自己快死掉了。
家裏有親戚探望。
我媽躲房間昏睡,隻由我爸出麵接待。
客人們帶來一堆補品,驅寒問暖一會,我聽見他們提到我——
「這孩子看著文靜,怎麼會突然這樣叛逆呢,唉......」
我爸冷冷說:「誰知道呢,她從小妒心就重。」
那人聽罷壓歎了口氣,用推心置腹的語氣道:
「你們夫妻以後還是多為自己著想吧,看看是趁年輕再要一個,還是去外麵認養一個......」
我沒聽見我爸接話,也不知他是點頭還是搖頭。
我臉上濕涼一片。
哥哥在的時候我多餘,哥哥不在後,這個家又需要其他小孩了。
還真是偏我來時不逢春。
客人走後,我想我也不應該再待家裏了。可才走幾步,我便頭暈目眩,撞在了鞋架上。
稀裏嘩啦的動靜後,我媽被吵醒,尖叫著撲過來拍打我的腦袋和肩背。我腦殼嗡嗡作響,跌坐地上,手掌被陶瓷碎片割傷。
痛......
可當看見那枚哥哥給我的平安玉也掉地上時,我顧不上手傷將它握在了手心。
血一滴一滴打在玉上,鮮豔而突兀。
爸爸匆忙趕來試圖控製失控的媽媽,房間亂成一鍋粥,我跌跌撞撞地爬起來,跑出了家門。
我像遊魂一般漫無目的地一個人走在大街上,走到雙腳發軟,最後竟是昏了過去。
再醒來已是在醫院。
醫生拿手電照了照我的眼睛,而後給我開了一長串的檢查。
我想要本想拒絕,但看醫生嚴肅的臉色,最終把到嘴邊的話咽下。
隔兩天去拿報告,結果給我當頭一棒。
醫生說,我腦子裏有顆惡性腫瘤,也就是腦癌。
醫生看著麵色蒼白的我,有些不忍:「聯係你家裏人吧,他們有知情權,積極治療的話,最長還能有兩年的時間。」
我猶豫了許久,還是給媽媽打了電話,沒人接。於是我又給爸爸打,漫長的等待後,才叫了一聲「爸」,就聽見他劈頭蓋臉地訓斥:
「白落落!你到底想怎麼樣,還嫌把我和你媽害得不夠慘嗎?」
我在奢求什麼呢?
我突然覺得自己的可笑。
「爸爸,我死了,你們會難過嗎?」
手機那頭愣了一下,接著便聽到我爸的嘲諷:「現在翅膀硬了,動不動就威脅父母,要把我們折磨到什麼地步才肯罷休?」
「我沒有......」
「你太讓我失望了,隨便你吧,你要實在想死我也不攔著。」
聽著那頭的掛斷音,我發了好久的呆。
太陽在一點點沉下去,恍惚間,我聽見有人叫我:「落落。」
有那麼一瞬,我似乎看見哥哥就坐在我身側的空位,可眨了眨眼,人影又消失不見。
原來是一場短暫的錯覺,我苦笑。
活著真是沒什麼意思,可如今,我也失去了像那夜一樣倉促赴死的勇氣。
我沒有其他去處,最終又站在了家門口。
拿鑰匙哆哆嗦嗦地打開門,卻看見我媽恰好站在了門邊,似乎是準備出門。
她的頭發亂糟糟的,臉也浮腫得厲害,看到我也是一怔,而後譏諷道:「喲,大小姐還懂得回來啊。」
她說著往我房間走去,很快便抱出一堆我的衣服,連著行李箱一塊丟了出去:「還回來做什麼,覺得自己很有能耐就滾啊,不要讓我再看見你!」
衣物在我腳邊散開,我握緊了手中的病曆:「媽媽......」
「閉嘴,我沒你這樣的女兒,你滾啊。」
我悲哀地笑了笑:「媽媽,是不是我也隻有死了,你們才不會那麼恨我?」
媽媽愣了一下,而後失智一般,尖叫道:「如果不是你,頌祺怎麼會走?為什麼死的不是你,你把我的頌祺還我!」
「好了,她愛幹嘛幹嘛去,你理她做什麼。」爸爸扶著媽媽的肩將她哄回屋。
我看著緊閉的大門,隻輕聲道:「爸媽,如你所願,往後不用看見我了。」
他們要我走,那我便走吧。
或許隻有在我走之後,這個家才能恢複平靜,這也是我能為他們做的最後一件事了。
我蹲下去收拾衣服,讓病曆變成了隻有我知道的秘密。
我在候車站睡了一夜。
第二日,在坐上最早的一班火車前,醫生給我打來電話:「白落落,你的情況現下可申請我院的一款試驗藥。你要不和家人商量一下?如果成功的話,生命延長5-10年以是很有可能的......」
「不用了。」我看著轟鳴著向這邊駛來的火車,打斷道:「我決定順應天命了。」
醫生著急了:「姑娘,即便不同意用試驗藥,以你的情況也該盡早來醫院治療才是。」
「謝謝提醒,但真的不用了。因為,我活著本就不算件幸事。」
心理醫生建議白母去遼闊的地方散心,於是白父請了幾天的假帶妻子去旅遊了。
然而幾天後回到家,夫妻倆麵對女兒空空如也的臥室門口,心裏都莫名有些不安。
「那丫頭脾氣真是倔,都幾天了還沒回來......」白父摸出了手機,盯著電話錄的界麵猶豫不絕。
白母瞧了他一眼,冷著臉回臥室關上門:「要打你出去打,別讓我聽見。」
於是白父走到陽台,正要按下撥號鍵,卻有一通陌生電話打了進來。
「你好,是白落落的父親嗎,我是她的主治醫生。」電話那頭的人說。
白父無措起來:「我是,她怎麼了?」
「您的女兒現在是腦惡性腫瘤三期,我院現在有一款試驗藥,效果好的話能延長5-10年壽命,隻是她拒絕了,並且至今未接受任何一種治療。我的勸說對她收效甚微,隻好聯係您了。」
「什......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