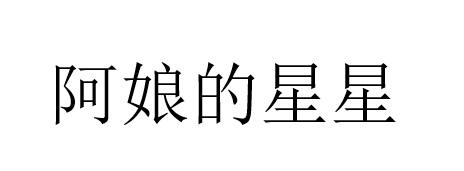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4章
回去的馬車上,阿娘一言不發。
她隻是抱著我,看著窗外飛速倒退的街景,好像要把這座繁華的京城,刻進眼睛裏,又好像要把它徹底忘記。
我的眼淚在眼眶裏打轉,但我不敢哭出聲。我怕阿娘聽了會更難過。
回到那個冷清的院子,阿娘開始收拾東西。
她把我們來時帶的那個小小的包袱打開,把我換下來的、帶著泥土氣息的舊衣服一件件疊好。
然後,她拿出了那個被踩壞的布老虎,坐在油燈下,一針一線地重新縫補。
燈光昏黃,映著她蒼白的側臉。
我看見她的手在抖。
那根阿爹為她削的桃木簪子,被她從發髻上取下來,輕輕放在了桌上。
做完這一切,她像是用盡了全身的力氣,突然劇烈地咳嗽起來。
「咳咳......咳咳咳......」
她捂著嘴,咳得撕心裂肺,小小的身子縮成一團。
我嚇壞了,連忙跑過去給她拍背:「阿娘!阿娘你怎麼了?」
等她終於停下來,我看見,鮮紅的血從她的指縫裏滲出來,染紅了她捂著嘴的帕子。
那紅色,比那天紮進她手裏的血珠子還要刺眼。
「阿娘!你流血了!我去找大夫!」我哭著就要往外跑。
「回來。」阿娘拉住了我,把染血的帕子藏進袖子裏,對我搖了搖頭:「阿娘沒事,老毛病了。」
我知道她在騙我。
以前阿爹打了勝仗,她也會咳血,但從來沒有這麼嚴重過。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夢。
夢裏,阿娘變成了一顆星星,掛在天上,離我好遠好遠。
我怎麼喊她,她都不理我。
我哭著從夢裏驚醒,發現阿娘正坐在床邊,看著我。
她的眼睛在黑夜裏亮得驚人。
「念念,」她摸著我的臉,聲音溫柔得像水,「如果有一天,阿娘帶你離開這裏,去一個很遠很遠的地方,你願意嗎?」
「願意!」我毫不猶豫地回答,「隻要和阿娘在一起,去哪裏都願意!」
阿娘笑了,眼角卻有淚滑落。
第二天,公主姨姨派人送來了一碗湯藥。
張嬤嬤端著那碗黑乎乎的藥,趾高氣揚地說:
「夫人,這是公主特意為您求來的安神湯。公主說您昨晚在宮宴上受了驚,喝了這藥,對您身子好。」
我聞著那藥味,覺得很嗆人,本能地不喜歡。
阿娘看了一眼那碗藥,眼神平靜無波。
她接了過來,對張嬤嬤說:「替我謝謝公主。」
等張嬤嬤走了,阿娘端著那碗藥,走到了院子裏那棵枯死的槐樹下。
我以為她要喝。
誰知,她手一斜,將那碗黑色的湯藥,盡數倒在了樹根處。
做完這一切,她像是下定了什麼決心。
那天晚上,京城起了很大的風,吹得窗戶呼呼作響。
阿爹沒有回來。
我聽說,他陪著公主姨姨進宮去了。
阿娘給我換上了我們來時穿的舊衣服,把那個小小的包袱背在身上,又把縫好的布老虎塞進我懷裏。
她牽著我的手,最後看了一眼這個冷冰冰的院子。
然後,她帶我走到院子中央,抬頭看著天上唯一一顆亮著的星星。
風吹起她的長發,她的聲音清晰而決絕,仿佛在立一個血誓。
「我準備好了。」
她對著星星說。
「把我給他的一切,我的運氣,我的壽命,我的所有......都收回去吧。」
星星沉默了很久。
然後,那個空靈的聲音再次響起,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歎息:
【你可想好了?契約一旦解除,永無挽回的可能。他會失去戰無不勝的氣運,會病痛纏身,大夏的國運亦會因此動蕩。】
阿娘笑了,風吹起她的衣角,她像一隻隨時會乘風而去的蝴蝶。
「我蘇遙,以血為誓,以魂為引,」她的聲音在風中飄散,卻一字一句,無比清晰地傳進我的耳朵裏,
「從今往後,與蕭決,與這個大夏,恩斷義絕,死生不複相見。」
她的話音剛落,我看見她猛地咬破了自己的指尖,一滴血珠飛向夜空,融入了那顆星星裏。
星星的光芒,瞬間黯淡了下去。
與此同時,遙遠的皇宮深處,傳來一聲尖銳的鐘鳴,仿佛有什麼重要的東西,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