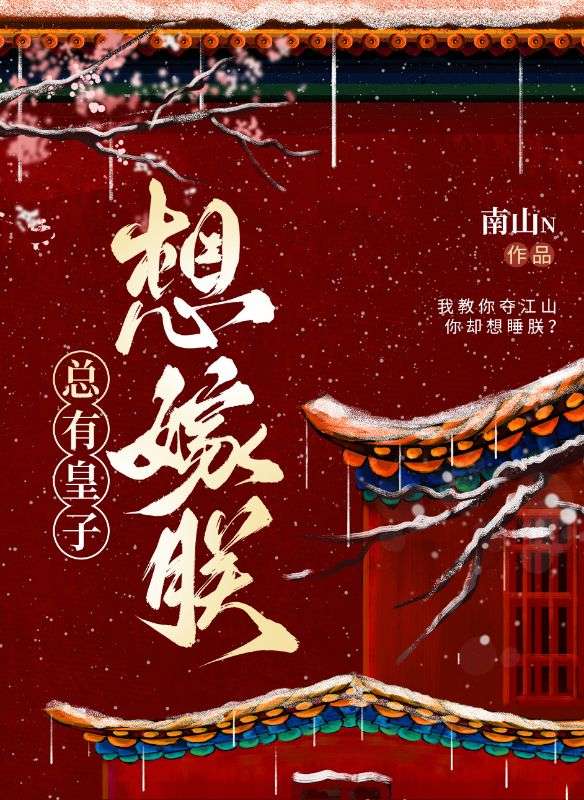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23章
看見
丁長卿的父親丁越原是禮部尚書,因受衛氏謀反之事牽連被革了職,好在丁家是在三族之外,沒有被抄家滅族,算不幸中的大幸。
丁長卿的禮賓司閑差自然也沒有了,如今閑賦在家,靠著舒王引薦,本想來東宮尋太子求個差事,沒曾想竟然看到如此鮮豔的一幕。
原來傳聞中太子和將不棄的關係都是真的啊。
不用猜也知道,定是因為東宮選妃之事,將不棄與太子生了嫌隙。若說男人對男人,沒有人比丁長卿更懂了。
他對太子誇下海口,定能讓將不棄對太子死心塌地。
太子正懊惱著呢,揮手讓人將他趕出去:“去去,你知道個什麼!”
丁長卿不死心,偷偷跟在將離身後。
出了東宮就是拱宸門,將離的情緒壞到了極點。
再沒有比現在更讓她覺得沮喪的了。
孟賀嶂進了京,本以為能從他身上撬開口子,沒想到他也是個倒黴蛋,一夕之間家眷被屠戮殆盡,怎麼看怎麼都不像出賣太傅的人。
再看看太子,不僅怯懦自私,還荒謬絕倫,她更覺得家國無望。
爹啊,大慶,要亡了!還做什麼帝師啊。
這一夜她獨坐攬月樓,豪擲千金,點了姑娘吹拉彈唱,喝了許多許多的酒。
也不知何時,丁長卿走了進來同她打招呼:“大人,怎麼一個人在這喝悶酒呢?”
他是個自來熟,將離同他飲了幾次,也算相熟,便招呼他坐下。
“長卿,別來無恙?”
“唷,您這話說的,就差脫一層皮了。”丁長卿悶頭一杯。
丁家為了洗脫附逆衛黨的嫌疑散盡了家財才得以保住身家性命;他的母親是衛貴妃的妹妹,深知自己衛氏女身份會牽連丁家,選擇了自縊。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再看看將家平步青雲,說不眼紅是假的。
可人家將不棄命好,出身好、長得好;不僅文章做得好好,他媽的武功還高。
救駕之功,這世間可沒幾個人有這福氣呢!
“將大人呐,我太羨慕你了!”
他都羨慕得流口水了。
“我自罰三杯。”將離雖然半醉微醺,但還沒全糊塗。
她半仰起頭,雪白的天鵝頸透著誘人的光澤,丁長卿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難怪太子也看上他了,的確是尤物,可比整條梨花巷最好看的小倌兒還要好看。
趁著她舉頭飲酒,丁長卿在她的酒壺裏撒了東西。
“尚書大人,如今您春風得意,若有什麼鞍前馬後跑腿的差事,也給我介紹介紹?我這實在是活不下去了。”丁長卿拎起酒壺,殷勤地為她倒滿。
酒醉迷人眼,將離眼前都出現了重影:“我?我何德何能?你該去求陛下才是。”
“哎,您別謙虛。三代帝師,您可是未來首輔啊。來,我敬您!”
將離醉了:“不提帝師!今日誰提帝師,我跟誰急!”
丁長卿哄著她:“好好,不提,不提。喝!不醉不歸!”
“不醉不歸!”觥籌交錯間,又開了好幾壇酒。
席間舒王帶著葵娘子也來飲了幾盞,閑聊了幾句,將離已經醉了七八分了。
梨花巷子外,玄暉買了火烤板栗遞給李承昊,“爺,這板栗非得要上這巷子買嗎?我記得咱們府門口就有小攤在賣啊。”
李承昊斜睨著他,丟了顆板栗在嘴裏嚼著:“板栗,它就得吃這條巷子裏烤的才香。你懂不懂啊!”
玄暉撇嘴,轉頭問崔無咎:“崔公子,真是這樣?”
崔無咎磕著板栗搖頭晃腦,“有些人啊,吃的是板栗,想的可未必是東西。長煦,我考考你,襄王有意、神女無心,出自何處?”
“呸!”李承昊吐了板栗殼,一腳踹了過去,“出自你的狗嘴,吐不出象牙的東西,還不早點滾回家去。”
“嘁!好心當成驢肝肺啊,我早就同你說了,將不棄高冷孤傲那是全雀都出了名的。你說他對你熱情,我看全都是裝出來的。他就是利用你。”
崔無咎站累了,隨地找了個門檻石坐了下來,邊說還邊招呼玄暉統一戰線:“阿暉,你說是不是?”
玄暉可不敢亂說話,胡亂塞了幾顆板栗進嘴裏裝死。
李承昊憋著一肚子氣沒地兒撒,眼睛不自覺地往攬月樓看,二樓包間開著窗一覽無餘,丁長卿的手都摸上了將不棄的手背了。
“你們懂什麼!他怎麼不利用你?不利用別人,偏就利用我?說到底還是因為我與眾不同。”
李承昊一腳踢掉腳步的小石子,砰的一聲,石頭衝出去老遠,砸到了一個過路人的腦袋。
那人慘叫了聲摸了摸腦袋,破口大罵:“哪個王八蛋打我?滾出來!”
崔無咎一臉同情地看著玄暉:“你家主子腦袋壞了。”
“長煦,這是病,得治!”
李承昊捏著拳頭作勢要揍他,嚇得他扔掉板栗,轉眼逃得沒影兒了。
那頭,將離在攬月樓小廝的攙扶下,上了丁長卿的馬車。
“尚書大人慢著點,我送您歸家去啊!”
“哎,這不是長煦嗎?”丁長卿看到他,遠遠打了個招呼。
將離醉眼朦朧沒有回頭,李承昊扭頭就走。
玄暉三步並兩步跑到前頭巷口解開馬韁繩,拉出兩匹馬,“尚書大人也是,一個人喝那麼多,連個長隨都沒帶。”
李承昊翻身上馬,剛跑出去幾步又調轉頭,對玄暉道:“你先回去。”
玄暉一臉茫然,“您呢?”
李承昊沒搭理他,自顧自策劃往丁長卿的馬車後追了出去。
馬車走得很急,轉眼即沒影了。
李承昊勉強順著地上的車轍,朝城南追了過去。
玄暉一路跟了上來,“爺,這方向不對啊。”
“當然不對!丁長卿這個狗崽子!走!”
就知道他沒好心!這廝好男風是雀都出了名的。
兩人趕到城南一個偏僻的農莊外,果然,外頭停著丁長卿的馬車,車夫不知跑到何處去了。
李承昊一腳踢破木門,丁長卿這個狗東西正在解將離的扣子。
長鞭如毒蛇吐信,打得他嗷嗷直叫:“總督,我和將大人你情我願的事,你這是做什麼?!”
“你情我願?”李承昊又狠狠抽了幾鞭,“你要不要撒泡尿照照自己?!”
他娘的,他堂堂北冥世子,一表人才、風流倜儻、瀟灑不羈將不棄都沒看上,會看上這肥豬一樣的丁長卿?!
簡陋的木板床上,將離麵色潮紅,眼半睜半闔;微敞的領口白肌似雪,直讓人挪不開眼睛。
“你喂他吃什麼了?!”李承昊牙根發癢。
“就就五石散,助助興的。我冤枉啊!”
李承昊氣得又抽了幾遍,對玄暉道,“他身上定還有,喂他吃,吃完了扔豬圈去!”
“總督,總督饒命啊!”丁長卿嚇得屁滾尿流,如竹筒倒豆子一般倒了個幹淨,“我這麼做,不是為我自己,是為了太子殿下啊!”
“太子殿下喜歡尚書大人,他倆蜜裏調油,是太子殿下讓我給大人下點助興藥的,大人,同我無關呐!”
丁長卿將自己推得一幹二淨。
他本是準備把人往東宮裏送的,可半道上實在是受不住這誘惑,想自己先開開葷,這才把人帶到城南的莊子裏。
李承昊懶得同他廢話,將離在朝他看呢。
他小跑到榻前,用披風將她裹上,打橫抱了出去。
將離似醒微醒,纖細的手指輕輕撫上李承昊的眉心,聲音又酥又麻:“長煦?”
“是。”李承昊咬著牙,托著她朝身上抻了抻,“喝了多少?跟死豬一樣沉。”
嗬,將離淡淡地笑了笑,眉心卻依舊緊蹙,隻是臉朝著他的胸膛蹭了蹭:“你看見我了?”
李承昊帶她翻身上馬,拉著馬韁繩。
將離正對著他跨坐,半個身軀靠著他,沒有了白日的冷漠,披風下的她又瘦又小巧,像隻黏人又可憐的貓。
李承昊心都軟了,哪還有半點氣,他低下頭看著懷裏的人,既無奈又哀怨:“想要看不見你,很難。”
“你怎知你看見的我,是我?”將離的手按在他厚實的胸膛,撐著臉仰頭看他。
那雙眼睛裹著濃重的酒意,連眼尾都在勾人心魄。
這個妖孽,又想要趁著夜色為非作歹了。
李承昊強壓著腹部的燥意,咬牙切齒:“你化成灰,我都認得!”
將離嘟著嘴,委屈地搖著頭,“你騙人,化成灰如何還能認得。你們都在騙人。我爹也騙人。”
提及太傅,她又低下頭嗚咽地啜泣著。
李承昊攬著她,輕拍了拍後背,聲音低到塵埃:“我送你回家。”
將離揪著他胸前的衣襟,瘋狂搖頭:“我不回去,那不是我的家。”
她掙紮著想要從馬上躍下,驚得李承昊收緊韁繩,勒馬停了下來,強健有力的手臂將她牢牢圈在懷中,穩如泰山。
“你想去哪?”他的聲音似乎從遙遠的銀河飄來,磁性又醇厚,低低地呢喃,勾著她的渴望。
五石散在酒的催發之下快速起效,將離伸手圈住李承昊的脖頸,抬著流螢般的眸子癡癡地看著他,聲如午夜魅魔:“敢不敢帶我回家?我要讓你看到我。”
李承昊的薄唇被她鼻息呼出來的熱氣吹得發顫,聲音如堵了棉花在喉間打轉,手不自覺地攥著馬韁繩開始僵硬,人都變得無比笨拙。
他好氣!怎麼三言兩語又敗下了陣。
一想到這,他粗起嗓子惡狠狠回道:“敢,怎麼不敢。”
秋末的夜風很涼,馬蹄疾馳在黑暗中,兩人的心跳逐漸同步。
她的手很涼,掛在脖上卻燙得如同烙鐵,李承昊幾乎是飛回了總督府,連馬都顧不上圈,抱著她就往寢房跑。
這個將不棄太壞太壞了。
他絕對不能這麼算了!
他惡狠狠地將人扔到床榻上,手指顫抖:“狗東西,你又想玩什麼把戲?有什麼招都給爺使出來,爺讓你見識見識什麼叫坐懷不亂!如今我劍術已成、道心堅定,絕不會再上你的當!”
將離的帽子都被甩掉了,發髻鬆散,黑發垂肩如緞;兩頰成了桃花麵,眸中春色無邊。
她隻是輕咬了下唇喊疼,李承昊登時恨不得扇自己兩耳光。
“罷了罷了!妖孽!”他恨死自己了。
全然鬥不過這個妖精!
打不過,隻能跑了!
他轉身拉開大門,將離低低恥笑:“原來你不敢。”
砰!李承昊狠狠合上門,順勢還插上門栓,氣得頭發都炸了。
“我警告你!別以為爺不敢動你!你再這麼看著我試試!”
將離從床榻起身,一步一步朝他走過去,唇角浮動冷笑,黑眸在燁燁燭火下逐漸變得癲狂:
“崔無咎不是會剖屍驗骨嗎?他有沒有告訴你,人褪去皮囊有二百零六骨,可披上人皮,確有一萬八千相。你是何相,我是何相?你眼中的我又是何相?”
她突然開始倒書袋念佛偈,李承昊雖滿頭霧水,可還是迎頭直視毫不退卻,“任你皮囊千萬張,我也認得你。旁人都是二百零六骨,你多一塊,腦後反骨。你這個黑心肝的,走到哪、幻成何相,我都認得你!”
將離眼圈微紅:“我黑心肝?你剖過?我也許無心呢!”
“無心?”李承昊氣不打一處來,伸手開始撕她衣裳領口,哧啦一聲,玉石扣子掉落在地上,砰地在地上打轉,又順著地麵不知溜向何方。
“好啊,取刀來,讓爺剖開來瞧瞧,到底是黑心,還是無心!耍我有癮是吧!”
將離目光挑釁:“來。不敢是小狗。”
“他娘的!”李承昊頭一昏,兩人互相扯起了衣裳,很快,外袍落盡,兩人都剩下一身雪白的交領裏衣。
李承昊死死握住她的手,眸光堅定如昨:
“我敢。你敢嗎?廢物點心,隻會躲。”
“我不躲。我要讓你看見我,真正的我。”
將離甩開他的手,迎著他熾熱的目光,解開腰帶、撩開裏衣,胸前層層捆紮的白布讓李承昊徹底呆如木雞。
他像一個雕像矗立在將離麵前,連呼吸都滯住了。
將離仰著頭,一層層鬆開棉布,長長的布條一圈圈地垂在地上,猶如層層剝開的洋蔥,秘密就這樣猝不及防又一絲不掛地展露在李承昊的麵前,讓他從極冰之地飛躍至火山之巔。
他的耳畔有聲音如潮水湧來:
“我,不是將不棄,我叫將離。看到了嗎,這才是我。我,叫將離。”
淚決了堤,委屈無所遁形。
堅硬的外殼之下裹著一個小女孩渴望被光照耀的怯懦。
她抽了抽鼻子,故意挑釁他:“看清了?!滾吧!”
“滾你大爺!”滾燙又粗糙的大手掐著她的腰,一把舉起她,將她扛在肩上;
沒等她反應,整個人又被甩在柔軟的床榻上。
那道厚實的身影根本不給她反抗的機會,如高牆頹塌,死死壓了上來。
“該死!該死!我早該想到的!”
那相同的臉,相似的眉眼;一個寡淡無趣,一個讓他如癡如狂。
大手撥開將離額間的亂發,李承昊瘋了似地吻她,失而複得、欣喜若狂。
粗啞的嗓不停地喊著她的名字,“你是將離!將離!”
“是,我是將離!”她的淚順著眼角落在錦被,開出了一朵朵絢麗的花。
吻到彼此都耗盡力氣,李承昊眼眶濡濕,深情又纏綿地望著她,眼裏拉出長長的絲線,一圈圈將彼此繞在一起。
將離醉意繚繞,再度伸手圈住他的脖子,將他的頭拉向自己,在他的耳畔吹著熱氣:“怕了嗎?”
“怕你爹。”粗啞的嗓,溫柔得不像話。
大手刻意抬高她的下巴,霸道又纏綿地覆上她的唇,直吻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
熱浪拍打著礁石,又激起千堆雪,他們在浪潮中緊緊相擁,再也不是天地的孤鴻。鶴鳴九皋、鷹逐長空,朝陽和路匍匐在他們的腳下;山河蜿蜒,歡樂奔騰地向著未知卻映著絢爛天光的盡頭。
“可以嗎?”他低低地在將離的耳畔呢喃,像一個巨大的熔爐,要將她融化。
她熱得透不過氣,翻身在上,學著他捏著下巴,“求我。”
他俊朗的眉眼噙著笑,半坐起,雙手掐著她的腰,如蜻蜓點水似的,親著她額頭、鼻尖,紅唇,一點一點向下:“求求了。”
他學她的語氣學得極像,將離笑了,“孺子,可教也。”
得到許可和讚美,他渾身爆發無窮無盡地力量,一個翻身又將她錮在身下。
再沒有過多的語言,他們在天地之間見證彼此最真實的一麵。
疼痛如鳳凰涅槃,枯骨一寸一寸長出血肉。
她抬手描著李承昊的眉眼,低聲呢喃:
“若非有你,我本無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