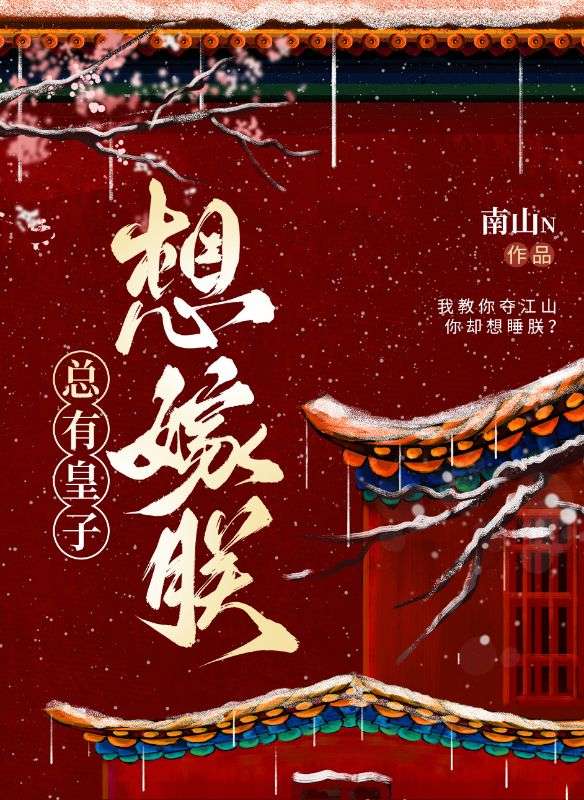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20章
確認
謝世忠笑得意味深長:
“噫!尚書大人也知道?前些日子的確是找了許多舞姬,但男人麼,尋常花樣膩了,也愛嘗新鮮。那些個小倌兒一個賽一個的好看,可不輸花魁娘子呢!要不改日同去?”
將離訕笑:“改日飲酒可以,這我可無福消受。”
謝世忠朗聲大笑,眉骨聳動。
潘德海出來看到他,立刻躬身相迎:“喲,司公來了,陛下正等著您呢。”
將離同他拱了拱手,告辭而去。
避暑山莊謝世忠雖姍姍來遲,但皇帝事後隻罰俸便罷,皇城司依舊牢牢握在他的手中,可見此人非同尋常。
這人麵上笑嗬嗬,實則城府極深,尤其是那雙細眼,縱然麵上笑意再深,都冷得像淬毒的刀,將離不敢輕易靠近,也不敢輕易得罪。
出了宮,她打發了雙慶後,帶著琉羽去了城郊的善堂。
慧修最近都在此處。
秋季多雨,馬上雨季要來了,最近善堂請人修繕屋簷及各處破損之處,她忙得團團轉。
“這回氣色倒是好些,藥還接著吃,知道嗎?”慧修摟著她,看了又看。
“記得,一天三頓忘不了,琉羽都盯著呢。”將離親熱地摟著她手臂搖了搖,“師父,瞧著大事快定了。隻等那孟賀嶂進京,我還有些話得問他。”
“萇茗也不知跑到哪裏去了,信鴿都找不著他。不然也好讓他去葉州再探一探。若真是屠光殺了太傅,直接剁碎喂狗!”
將離點頭,“葉州有問題,為何孟賀嶂做了二十年的師爺卻從未對朝廷提過?湧安收買葉小東換信,二皇子卻至死不認。若不是他指使,又會是誰呢?現在二皇子一派已經沉戟,死無對證,走進了死胡同。唯一得到好處的,真就隻有皇帝了。湧安難道是為皇帝辦事?我總覺得這裏頭哪不對,可我一時又想不明白。”
能為皇帝辦這樣機密的大事,怎麼也輪不到湧安吧?
謝世忠和他旗下的皇城司又不是擺設。
這便是將離想不明白的地方。
慧修對皇帝沒什麼好感,自古帝王皆心狠手辣,她認同將離的看法:
“伴君如伴虎,當年若沒有你爹授他詩書,他如何能成為大慶帝王。真是狡兔死、走狗烹。按我們話說,就是白眼狼。”
將離眉眼淡淡:“或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呢。爹雖事事謹慎,可將家那些個狗東西沒一個不招搖的。”
慧修深以為然,她拍了拍將離的手背,“走,去瞧瞧湧安老娘吧,在裏屋。”
她剛想陪著將離一道進去,身後有個娘子喚她:“慧修師傅,這個竹子抬去哪裏?”
“哎喲王娘子,你放著放著,我來,別閃著腰了。”
將離回身一看,是個滿臉紅潤、腰背憨實的婦女,正用粗布擦著汗,“不妨事,我最不值錢的就是力氣了。”
慧修爽朗一笑,兩人一前一後忙活去了。
將離對琉羽道:“這個娘子好生爽利,倒是同師父投緣。”
“也是個可憐人。他相公淹死了,家裏仨孩子嗷嗷待哺,平日就在街市上賣菜討生活,師父接濟她,她也懂得感恩,空閑了來善堂打下手。”
將離邊走邊點頭:“師父說得很對,女子嫁了人便是二次投胎,誰也不知自己的命運會如何,惟有活一日算一日,尤其是有了孩子做羈絆,哪能如未出閣時那般如意自在。這王娘子既同師父投緣,便是自己人,咱們能幫多少是多少;等有了錢,再再多建幾個這樣的善堂。”
將離邊說邊想起許久未見的平陽侯夫人斐柔,不知她近來如何了。
“斐柔近來可去觀裏燒香了?”
琉羽搖頭,“來過一次,師父本想與她聊幾句但伯府的人催著走。”
高門大院門戶森嚴,她幾次上門拜訪都不得入,將離惟有歎息:“希望姐姐安好。”
西屋門一開,湧安的娘抬著渾濁的眼往外看,視線飄忽。
將離心一頓,與琉羽對望,瞎了?
琉羽用口型:是啊,我沒說過嗎?
將離搖頭,她小步走近:“大娘,我是湧安的朋友,來看您了。”
“哎,哎,小安子可好?他跟使團出去可回來了?”老太太伸手茫然地抓著,將離握住她枯槁粗糙的手。
“湧安挑了大梁,這一時半會還回不來,您安心在這住著啊。”
老太太一臉喜色:“好,好,小安子有出息就行。我這身老骨頭早就該見閻王了,沒得連累他。你若見到他,記得幫老婆子帶句話,多聽將太傅的指點,要記得感恩。當年若不是太傅救了我們母子,我們哪有今日啊。”
將離一時有些緩不過來,“我父親救了你們?何時?”
“啊!原來您是太傅的公子?!當年湧安爹死了後,他們家裏人就把我們母子趕出去了。大雪天,我們無處可去,路上遇見太傅,他真是個大好人!不但給我們母子倆找了住處,還塞了十兩銀子。後來湧安大了,還提攜他進宮當差,我們母子這才過上了太平日子啊。前幾年大疫,老婆子差點死了,又多虧了太傅贈藥,我才又活了過來。我這條命都是太傅的。隻可惜老婆子如今眼也瞎了,腿也殘了,隻能日夜誦經,為太傅祈福了。”
將離唏噓,湧安母子同將正言還有這麼一段情分。
可既如此,湧安又怎麼會為害將正言呢?
他究竟受何人指使?
事情越發撲朔迷離了。
近日無事,將離將琉羽留在了善堂幫慧修,自己則慢悠悠地踏著月光踱步回去。
她的腦子很亂,看似線索增加,實則都是一個個無解的線頭,越抽越亂。她要好好想一想,這中間到底還有什麼她不知道的隱情。
不知不覺走到了海棠巷,這是梨花巷的後巷,很窄,昏暗無光。
她敲了敲腦袋,怎麼走到這來了。
剛想折返,人就被一堵高牆擋住,抵在牆壁上。
“李承昊?”將離皺了皺眉,“你又喝多了?”
“這兩日我一直在想,為何是這樣?”他垂著頭低喃,“為什麼呢?子夏?”
將離哭笑不得,這個人喝醉了說話顛三倒四,她完全聽不懂,“什麼為什麼?”
“你閉嘴,不要說話。”他嗡聲嗡氣,十足霸道,“我要確認一件事。”
將離仰起頭望著他,滿是不解,“確認什麼?”
李承昊一手撐著牆壁一手捏住了她的下巴,“你別動。”
將離還未來得及反應,他的唇便覆了上來,鼻息熾熱,酒氣衝天。
將離瞪大了眼睛,腦海一片空白。
她死死抵住牙關,方寸大亂,可李承昊今夜像瘋了一樣癡纏不放,不僅用舌頭撬開她的齒關,還長驅直入,吻得霸道又深沉,連一絲喘氣的餘地都不給她。
她用力推,可寬厚的胸膛像銅牆鐵壁,紋絲不動;漫長的吻彷如幾世那麼長,直至最後的最後,彼此氧氣耗盡,她終於獲得一線喘息,狠狠咬了李承昊的下唇,推開了他。
“你瘋了!”將離不可置信。
李承昊摸著唇,表情如困獸狼狽又痛苦,“你說對了,我瘋了。我真是瘋了,將不棄!”
世上那麼多男女,怎麼偏偏就對他動了心?
該死的,他到底給自己下了什麼蠱?
“你告訴我,你對我下了什麼降頭?為何我會起這個心思?旁的人,女子也好,男人也罷,全然不行,唯獨對你。唯獨隻有你!”
他像是入了魔一樣,滿腦子都是他。
這個人太壞了,不光占據他的心,還毫不客氣地出現在不可描述的夢裏。
他寬大的雙手鄭重地捧著將離的臉,猶如對日月星辰發著誓:
“我確定了。是你,獨獨是你,無關男女。將不棄,我對你動心了。你……”
“你什麼你!瘋子!”
將離心臟狂跳,猛地推開他,飛也似地逃走。
“我認定你了!你休想逃!”
李承昊的聲音回蕩在巷子久久不散,像個魔咒讓將離魂飛魄散。
他是瘋了嗎?!
…………
將離一路跑回翠竹軒,三魂丟了七魄。
將不棄從鬆濤院過來,見她如此慌張,不由得擰眉:“怎麼跟見鬼了似的。”
“見鬼了,是見鬼了!”將離臉色煞白,摸了摸胸口,“夜路走多了,果然是見鬼了。將不棄,明日你自己上朝吧。我,我要告假幾日。”
“為何?你又做了什麼虧心事?”將不棄心一咯噔,“快說!”
將離拎起桌上茶壺,對著壺嘴咕咚咕咚飲了個痛快,才道:“今日我為崔永真求情了。”
“混賬!誰讓你……”將不棄氣得想要站起來捏死她。
“稍安勿躁!”將離白了他一眼,“陛下沒有責怪,寬恕了崔永真。不過,我同太子在東宮稍有爭執,還是緩幾日再見吧。如今大勢已定,尚書大人你登閣拜相亦指日可待,難道不想親自站在朝堂呼風喚雨?”
這句話說到將不棄的心坎上,他的確是這麼想,也想試一試。
隻是這個腿還站不起來,他猶豫該尋什麼借口。
將離斜睨了眼,看穿了他的心思,揶揄道:“陛下如今腿腳亦是不便,你的腿疾,倒是因禍得福。臣子與君同憂,尚書大人又走在了群臣的前端。”
她滿嘴陰陽怪氣,將不棄有些惱怒,可不好發作,“正好選妃一事我要同太子細細斟酌,那你就歇幾日吧。”
他轉頭離開,詭譎陰毒的笑隨即浮上唇角。
若重返朝堂順利,將離即可殺。
二皇子封在木箱整整七日。
從一開始的抓撓、哀泣漸至無聲,直至箱子開始透出腐爛的氣味。
這氣味如同海灘暴曬九九八十一天的死魚彌漫整個大殿,繞梁不絕,又鑽入每一個入殿議事的朝臣鼻子裏,像鈍刀子割著肉,一分一秒都是折磨。
秋涼起風,本該爽朗溫怡,可朝臣們手持笏板如立於凜冬大雪,脊背發寒。
將不棄坐著輪椅來上朝,皇帝隻抬了抬眼皮隨口一問,便不再提了。
倒是李承昊愣了半晌,想不明白他怎麼又瘸了腿。
退朝後他想問,但將不棄被東宮的人帶走了,他隻能悻悻作罷。
如此,接連著幾日上下朝,除了大殿臭哄哄的,一切皆如常。
將不棄懸著的心終於放了下來。
眾臣皆沉浸在腐朽的死亡之中,一個個灰敗著臉,唯獨李承昊眉頭皺得像山川大嶽,沉重而憤懣。
將不棄竟然視他於無物,非但對他的深情凝視毫無反應,竟然像不認識他似的,同他生疏又冷淡。
他這個狗東西!猖狂得誌,小人!
李承昊幾次想要堵著他,要麼是同僚人來人往,他又坐在輪椅上,總覺得隔著距離,不好親近;要麼就是看著他與太子聊得熱火朝天。
想起那日在芙蓉山莊將不棄為了救太子幾乎丟了半條命,他就像是蔫了的公雞似的,無精打采。
如此又過了兩日,他似乎想通了,又跟打了雞血似的,開始操練起禁軍和殿前司了。
跑馬、搏擊、射箭、負重奔跑,日日加碼,玄暉累得跟狗似的,忍不住為大夥兒求情:“爺,今日可否少跑幾圈?”
“你瞧瞧你,來雀都才多久,身子骨就廢了。跑起來,今日沒跑完二十圈不許吃飯!”
禁軍的將士們紛紛打聽,總督這是怎麼了?
玄暉悶頭跑,怎麼了?
他怎麼知道怎麼了!
將離躲在翠竹軒幾日,心緒難定,便去善堂找慧修。
師父無所不能,定能給她指一條明道的。
可慧修不在,連琉羽也不在。
今日她依舊一身白色海浪紋箭袖騎馬裝,但怕被人認出,特地戴了頂鬥笠帽,遮陽又擋臉。
剛進善堂,迎麵便撞上了王娘子。
她滿頭都是汗,紅光滿麵的,像是一路小跑而來,見到她一拍大腿:“喲,我正要去找您呢!慧修師父說城郊外東郭村那有個荒廢的廟,她想把地買下來,讓我趕緊回來,請您去一趟,一塊兒參謀參謀呢。”
將離一笑,走到水缸旁,給自己舀了杯水,也給她遞了一杯:“師父看好買就是了,沒必要我參謀。琉羽呢?”
“琉羽姑娘昨日去乾縣了,說是去請什麼夫子,給咱們慈幼局的孩子們開蒙講學呢。”王娘子咕嚕咕嚕一飲而盡,用袖子擦了擦嘴,“咱們走吧,沒得讓慧修師父等呢。”
左右也無事,將離點頭應承了。
她進屋跟湧安的娘打了個招呼。
湧安的娘本想請她幫個忙去趟梅隴村。
這些年她替湧安攢下不少銀子,都偷偷埋在家中那個雞窩下邊,想著善堂和慈幼局都缺錢,眼下又沒到娶媳婦的時候,想取些出來給慧修。
可她還沒來得及張口,就聽得將離跟王娘子走了,隻得作罷。
“馬車太慢,跟我騎馬走。”
將離讓王娘子隨她上馬,一道出城。
城門口,玄暉指著她的身影對李承昊道:“哎,爺,您看那個人像不像將不棄?他腿傷又好了?嘖,那個胖娘子是誰?”
李承昊早就看見了,隻消背影他都認得這是誰。
他娘的將不棄,嫌棄他也就算了,找個肥婆算怎麼個事兒。
他還不如肥婆了?!
他心裏氣炸了天,有苦說不出:“他要吃屎你管得著麼!”
玄暉無端挨了頓罵,撓著頭萬分委屈:“我沒說他吃屎啊。”
東郭村在城郊三十裏,策馬也就半個時辰。
那破廟在一個村口的半山腰,破是真破,外頭都掛蜘蛛網,周遭都是樹,安靜倒是挺安靜的。
“前頭有河,下頭就是村子,這地方還行。多少銀子?”將離背著手跨進廟門,朝裏頭喊,“師父?”
裏頭無人響應。她轉身想問王娘子,廟門啪地一合。
昏暗的大殿落下一張巨大的網,將她死死網住後,唰唰落下幾個蒙麵的黑衣人。
“你們是誰?!我師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