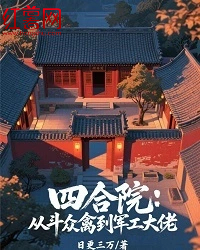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17章
當清晨的第一縷微光,艱難地刺破京城上空厚重的鉛雲時,軋鋼廠後院的這座“設備墳場”,已經徹底變了模樣。
那個由秦洛峰親手挖出,深達一米五的地基坑,此刻已被一種色澤灰暗、質地粗糙,卻顯得異常堅實的自製混凝土填滿。
水泥與煤渣,在秦洛峰那近乎於煉金術般的配比下,完成了它們的“涅槃”,緊緊地包裹著那些從廢舊建築上拆下來的螺紋鋼筋,凝固成了一塊沉默而堅不可摧的磐石。
“總師,成了!”
王敬山用手掌摩挲著那尚帶著一絲潮氣的混凝土表麵,感受著那份超乎想象的硬度,渾濁的老眼中,閃爍著孩童般的光彩。
這三天,他仿佛親身經曆了一場神跡。
他看著秦洛峰如何用最簡單的杠杆原理和滑輪組,將那重達數噸的蒸汽機和飛輪,從倉庫的角落裏,一步步地挪移到了地基旁;他看著秦洛峰如何用一堆廢棄的鐵管和耐火磚,搭建起一個簡陋卻高效的“土法高爐”,為後續的零件修複做著準備。
秦洛峰的每一個動作,都充滿了科學的嚴謹與藝術的美感。
他仿佛不是在跟一堆廢鐵打交道,而是在指揮一場由齒輪、杠杆和力矩組成的盛大交響樂。
“這隻是第一步。”
秦洛峰直起身,擦了擦額頭的汗珠,目光落在了那兩頭沉睡的鋼鐵巨獸身上——老舊的往複式蒸汽機,和那個直徑超過兩米的巨大飛輪。
“接下來,才是硬仗。我們要把它們徹底拆解,清洗,修複每一個磨損的零件,更換掉所有老化的密封件。這個過程,不能有半分馬虎。”
秦洛峰的聲音,一如既往的平靜,卻帶著一股不容置疑的專業與權威。
“明白!”
王敬山用力地點頭,他現在對秦洛峰的話,已經到了奉若圭臬的地步。
然而,就在兩人準備大幹一場時,一個最現實,也最棘手的問題,擺在了麵前。
“總師,”
王敬山指了指那台蒸汽機上那些鏽死的大號螺栓,麵露難色,“這玩意兒,沒個大號的套筒扳手,光靠我們手裏這兩把活絡扳手,怕是卸不動啊。還有那飛輪的軸承,得用專門的拉拔器才行。這些工具......一號車間的工具庫倒是有,可那個閆算盤......”
話沒說完,意思卻很明顯。
他們被卡在了最基礎的工具上。
秦洛峰的眉頭微微皺起,隨即又舒展開來。
“工具庫裏有的,是‘標準件’。”
他淡淡一笑,“但我們要做的,是‘非標’的活兒。王師傅,您忘了?我們現在,是‘技術攻關小組’。我們的任務,就是解決別人解決不了的問題。既然沒有趁手的工具,那我們自己造。”
說著,他轉身從一堆廢料中,抽出了一根長長的,材質極佳的高碳鋼撬棍,在手裏掂了掂。
“這根撬棍,退了火,足夠我們打造出幾把最頂級的重型扳手。至於拉拔器......”
秦洛峰的目光,落在了倉庫角落裏,一台廢棄液壓機那粗壯的活塞杆上,嘴角勾起一抹自信的笑容,“用它,我們可以做一個簡易的液壓拉馬。雖然簡陋,但力量,絕對夠用。”
自己造工具!
王敬山再一次被秦洛峰那天馬行空卻又無比務實的思路給震驚了。
他感覺自己的腦子,在這三天裏,比過去二十年轉得還要快。
兩人說幹就幹。
升火,鍛打,淬火,研磨......
這座沉寂的倉庫,仿佛變成了一個小型的兵工廠。
王敬山那爐火純青的鍛造技藝,與秦洛峰超越時代的工具設計理念,完美地結合在了一起......
與此同時,廠長辦公室。
楊興國的秘書小張,正恭敬地站在辦公桌前,彙報著他這三天“潛伏”觀察到的情況。
“......事情的經過,就是這樣。秦洛峰同誌和王敬山師傅,這三天幾乎沒有離開過倉庫。他們沒有申請任何特殊材料,所有的東西,都是就地取材。他們用廢棄的煤渣混合舊水泥,澆築了地基;他們正在用廢舊的撬棍,自己鍛造工具......”
小張的語氣中,充滿了難以置信。
他原本以為,秦洛峰拿到廠長的“尚方寶劍”後,會大張旗鼓地去申請物資,去彰顯權力。
卻沒想到,對方竟然選擇了這樣一條最艱難,也最不可思議的道路。
楊興國靜靜地聽著,手指有節奏地敲擊著桌麵。
他那副黑框眼鏡後麵的雙眸,閃爍著越來越亮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