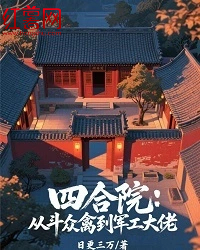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12章
三天。
整整三天,秦洛峰和王敬山就像兩隻在時間夾縫中生存的鼴鼠,將自己徹底埋葬在了這座名為“設備墳場”的鋼鐵地宮之中。
倉庫那扇沉重的鐵門,如同一個世界的界碑。
門內,是蒸汽與齒輪的狂想曲,是鋼鐵與火焰的交響詩;門外,依舊是那個充滿了雞毛蒜皮與人情世故的,1956年的冬天。
“哐當——!”
一聲巨響,伴隨著王敬山一聲壓抑的痛呼,打斷了倉庫內富有節奏的敲擊聲。
秦洛峰猛地回頭,隻見王敬山捂著自己的腰,齜牙咧嘴地靠在一台廢棄的刨床上,腳邊,是一根剛剛從手中滑落的沉重扭杆。
他的臉色有些蒼白,額頭上布滿了細密的汗珠。
“王師傅!”
秦洛峰快步上前,一把扶住他,“您沒事吧?”
“沒事,沒事......”
王敬山擺了擺手,試圖站直身體,但腰部傳來的劇痛卻讓他倒吸一口涼氣,“他娘的,老了,不中用了。想當年,老子一個人能扛著一根炮管跑半裏地......現在搬根破軸,就閃了腰。”
秦洛峰眉頭緊鎖。
他知道,這不是一句玩笑話。
王敬山畢竟年近花甲,這三天不眠不休的高強度體力勞動,對他身體的消耗是巨大的。
他們靠的,是王敬山那口不甘落幕的英雄氣,和秦洛峰帶來的希望之火,硬生生撐著。
但精神可以亢奮,身體卻不會撒謊。
“盤古之心”計劃才剛剛開了個頭,王敬山這個絕對的核心,就先倒下了。
秦洛峰扶著王敬山坐下,又從自己的水壺裏倒了點水給他。
看著老人那張滿是油汙和疲憊的臉,秦洛峰的心中湧起一股暖流,也升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緊迫感。
他不能讓這位燃燒自己照亮他計劃的老人,就這麼垮掉。
“王師傅,今天就到這吧。”
秦洛峰不容置疑地說道,“活兒是幹不完的,身體是革命的本錢。而且,我們的‘彈藥’,也快見底了。”
秦洛峰指了指角落裏那個空空如也的布袋。
他們帶來的窩頭和鹹菜,早在昨天就已經吃完了。
這一天,兩人是餓著肚子在幹活。
王敬山喘勻了氣,苦笑道:“總師,這兵馬未動,糧草先沒了。廠裏的食堂......怕是不好回去了。”
他知道,秦洛峰在食堂把傻柱得罪得那麼狠,回去打飯,還不知道要被怎麼刁難。
“食堂?”
秦洛峰笑了笑,眼神裏卻透著一絲冷意,“那種地方,不去也罷。咱們吃點好的。”
他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灰塵,對王敬山道:“您在這兒歇著,我去去就回。咱們今天,吃肉喝酒!”
說完,他便拉開那根抵門的槽鋼,推開大門,走入了久違的陽光之下。
刺眼的陽光讓他微微眯起了眼,也讓他從那個蒸汽與鋼鐵的幻想世界,瞬間回歸到了現實。
秦洛峰沒有去廠區,而是繞著廠區圍牆,朝著一處偏僻的後門走去。
他的兜裏,揣著之前係統獎勵的,還沒怎麼動過的二十塊錢。
在這個工人月平均工資隻有三十來塊的年代,這筆錢,算是一筆不小的巨款。
穿過一條滿是煤灰的小巷,空氣中,一股濃鬱而霸道的肉香,混合著淡淡的酒糟味,直往鼻子裏鑽。
巷子盡頭,是一家沒有任何招牌的小飯館。
門口隻掛著一個歪歪扭扭的木牌,上麵用墨寫著兩個字:“老白”。
這裏,是軋鋼廠老工人們才知道的“秘密據點”。
店主老白,是個沉默寡言的中年人,一手醬肉的絕活,能讓最挑剔的老饕都讚不絕口。
更重要的是,他這裏,收錢,也收各種票,甚至在關鍵時候,還能“通融”。
秦洛峰推門進去,小店裏隻有三四張桌子,煙霧繚繞,幾個穿著工裝的老師傅正在喝酒劃拳。
“喲,這不是小秦師傅嗎?”
一個眼尖的師傅認出了秦洛峰,立刻熱情地打招呼。
秦洛峰在食堂那番“定量勺”的壯舉,早已讓他成了普通工人眼中的英雄。
秦洛峰笑著點了點頭,走到櫃台前。
櫃台後,那個叫老白的店主,正低著頭,用一把小刀,慢條斯理地剔著一塊巨大醬骨上的肉。
他剃得很專注,仿佛那不是一塊骨頭,而是一件藝術品。
“老板,二斤醬肉,一條大骨,再打二斤散裝白幹。”
秦洛峰開口道。
老白的手微微一頓,終於抬起了頭。
他有一雙很平靜的眼睛,眼角的皺紋很深,像是能看透人心。
他打量了秦洛峰一眼,又低頭看了看他滿是機油和鐵屑的雙手,以及那身明顯不合身的,沾滿了灰塵的工裝。
“小夥子,看著麵生啊。”
老白的聲音,和他的人一樣,平淡無奇。
“剛來的。”
秦洛峰回答。
老白沒再說話,拿起一張油紙,麻利地稱了二斤醬肉,又將那條剔得幹幹淨淨的大骨棒和肉一起包好,最後從一個巨大的酒壇裏,舀出滿滿一葫蘆白酒。
“一共三塊五,外加一斤糧票,半斤肉票。”
秦洛峰爽快地付了錢票。
就在他拎著東西準備轉身離開時,老白卻突然開口了。
“你手上那股機油味兒,”
老白的聲音依舊平淡,卻讓秦洛峰的腳步瞬間停住,“不是咱們廠裏蘇式機床上的‘T22’號油。倒像是......德國克虜伯工廠,戰前用的‘VB5’號防鏽油。那油,現在可不好找了。”
秦洛峰的心,猛地一沉!
他霍然轉身,死死地盯著眼前這個貌不驚人的中年男人。
他的雙手,確實在修複那台希斯母機時,沾上了其內部殘留的,早已凝固的防鏽油。
那種味道,極其細微,連王敬山自己都未必能分辨出來,這個小飯館的老板,怎麼可能一口道破?
老白卻仿佛沒有察覺到秦洛峰的驚駭,依舊低著頭,用小刀刮著指甲縫裏的肉末,自言自語般地說道:“那油啊,金貴。當年在沈陽兵工廠,也隻有幾台從德國運來的母機,才配用那玩意兒。可惜了,後來都讓小鬼子給搶走了......”
他的聲音裏,帶著一絲若有若無的悵然。
秦洛峰的後背,已經滲出了一層冷汗。
這個老白,絕不是一個簡單的飯館老板!
他也是從那個時代過來的!
而且,他接觸過核心設備!
“老板,說笑了。”
秦洛峰的大腦飛速運轉,臉上卻恢複了平靜,“我就是在後院倉庫裏瞎鼓搗,沾上的味兒。什麼油,我不懂。”
老白抬起眼,深深地看了秦洛峰一眼,忽然笑了。
那笑容裏,有欣賞,有釋然,還有一絲不易察覺的寂寥。
“是不懂,還是不能懂,你自己心裏清楚。”
他將手中的小刀往桌上一插,說道:“那條骨頭,算我送你的。拿回去,給你家老爺子......好好補補。別年紀輕輕的,就把一身的本事,都耗死在那些廢鐵上了。”
說完,他便不再看秦洛峰,轉身走進了後廚。
秦洛峰拎著沉甸甸的醬肉和白酒,站在原地,沉默了良久。
這個老白,看穿了一些東西,但他似乎沒有惡意,反而像是在提醒,或者說,在惋惜。
秦洛峰沒有再多說什麼,轉身離開了小店。
但他知道,這個叫“老白”的男人,已經被他列入了需要高度關注的名單。
當秦洛峰提著酒肉,回到那座充滿鐵鏽味的倉庫時,迎接他的,是王敬山那雙亮得像燈泡一樣的眼睛。
“肉!酒!”
王敬山激動得差點從地上跳起來,他一把搶過酒葫蘆,拔掉塞子,狠狠地灌了一大口,辛辣的酒液順著喉嚨燒下去,讓他發出滿足而舒暢的哈喇聲。
“痛快!他娘的,痛快!”
秦洛峰笑著將醬肉遞過去,兩人就著這滿屋的機油味,大快朵頤。
一口肉,一口酒,所有的疲憊與酸痛,仿佛都在這一刻,被這最原始的能量和快樂所驅散。
酒過三巡,肉過五味。
王敬山的話也多了起來,他指著那台“盤古”,眼中放光:“總師,等咱們這‘蒸汽之心’弄好了,第一件事,就是要給它配上一把好刀!我跟您說,咱們廠裏,還有寶貝!”
“哦?”
“在熱處理車間,有一塊當年從東北繳獲來的,日本人留下來的高速鋼!據說是給‘大和’號戰列艦的主炮炮管做膛線刀用的,寶貝得很!一直鎖在保險櫃裏,誰都不給用。咱們得想辦法,把它弄出來!”
秦洛峰聽著,心中卻在暗暗盤算。
老白的話,給他敲響了警鐘。
他和王敬山躲在這裏,自以為天衣無縫,但這個世界上,沒有不透風的牆。
他們的行動,已經開始在水麵上,泛起了一絲微不可查的漣漪。
“王師傅,”
秦洛峰打斷了他的話,神色變得嚴肅起來,“寶貝的事,先不急。我出去這一趟,發現一個問題。”
“我們的行動,可能需要加快了。而且,我們不能一直躲在這裏。”
秦洛峰沉聲道,“我們需要一個‘名義’,一個能讓我們光明正大,接觸到那些‘寶貝’的名義。”
王敬山愣住了,酒也醒了一半。
就在這時,倉庫那扇沉重的鐵門外,隱隱約約地傳來了兩個人的說話聲。
聲音不大,但在這寂靜的後院,卻異常清晰。
一個是車間主任劉建國,另一個聲音,陰沉而又充滿了“關切”,秦洛峰一聽就知道,是易中海!
“......劉主任,你可不能犯糊塗啊!那個秦洛峰,年輕氣盛,不知天高地厚,你讓他一個人在倉庫裏胡搞,萬一出了安全事故,這個責任誰來負?我這也是為了你好,為了咱們車間好啊!”
劉建國似乎有些不耐煩:“行了老易,我知道分寸。秦洛峰那孩子有本事,我相信他。”
易中海的聲音壓得更低了,充滿了蠱惑性:“有本事?我看是有點邪門歪道!劉主任,你可想清楚了,你這麼護著他,廠裏有些人,可是會不滿意的。比如說......李副廠長。你最近,是不是感覺自己手上的活兒,不太順手了?”
倉庫內,秦洛峰和王敬山的臉色,瞬間沉了下來。
王敬山握著酒葫蘆的手,青筋暴起。
而秦洛峰,則緩緩地站起身,走到門邊,透過門縫,看向外麵那兩個正在“交心”的身影。
他的嘴角,勾起一抹冰冷至極的弧度。
他知道,他那個需要的“名義”,似乎有人要主動送上門來了。
“易中海。”
“看來,不把你這塊最礙事的絆腳石徹底踢開,我的‘盤古’,就永無寧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