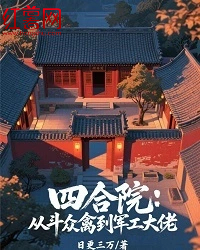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11章
蒸汽朋克?
王敬山咀嚼著這個從秦洛峰口中吐出的,聞所未聞的古怪詞彙。
“總師......您是說......”
王敬山的聲音幹澀,他指了指那台老舊的往複式蒸汽機,又指了指那台代表著人類工業文明巔峰的希斯母機,喉結艱難地滾動了一下,“您是要用這頭隻會喘粗氣的鐵牛,去拉動......那架需要繡花的馬車?”
這個比喻,粗俗,卻又精準到了骨子裏。
“沒錯。”
秦洛峰的笑容裏,帶著一種瘋狂的自信,“電,是現代工業文明的血液,是馴服的,是可控的,是優雅的。但我們現在沒有。可我們有比電更古老,更磅礴,更......富有力量的東西。”
他走到那台鏽跡斑斑的蒸汽機前,用手掌感受著那冰冷鑄鐵外殼下蘊藏的潛力。
“那就是蒸汽!是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怒吼!是推動人類邁入現代文明的第一股力量!”
他的聲音在空曠的倉庫裏回蕩,充滿了煽動性,“它粗暴,它不穩定,它難以駕馭。但王師傅,這世上,沒有劣等的動力,隻有蹩腳的工程師!電能做到的,蒸汽,通過另一種方式,同樣能做到!”
王敬山眼中的迷茫,被秦洛峰話語中的火焰迅速點燃,化為了技術人員特有的亢奮與狂熱。
他瞬間就洞悉了這個計劃的核心難點。
“可......可是精度!”
王敬山急切地說道,“蒸汽機的活塞往複,會帶來劇烈的震動和扭矩波動!這種波動,哪怕隻有一絲一毫,傳遞到車床主軸上,都會被放大成災難性的誤差!我們要做的是微米級的活兒,不是開火車!”
“所以,我們不直接連。”
秦洛峰胸有成竹,他撿起一根鐵條,在滿是灰塵的地麵上迅速地勾畫起來,一個遠超這個時代的動力傳動係統草圖,躍然地上。
“看這裏,”
秦洛峰指著草圖,“我們需要一個獨立的動力基座,用最深的樁基,把它和‘盤古’的床身徹底隔離開,消除震動傳遞。”
“然後,是傳動。我們不用齒輪硬連接。我們用它!”
秦洛峰指向倉庫角落裏,一台廢棄的德國紡織機上那幾條已經開裂,但主體尚在的牛皮傳動帶,“用最原始,也最有效的皮帶傳動!長距離的皮帶,本身就是最好的震動緩衝器!”
“最關鍵的,是這裏!”
秦洛峰在草圖的中央,畫下了一個巨大而厚重的圓形,“一個超大質量的飛輪!王師傅,您知道,當一個物體的質量大到一定程度,它的轉動慣性,將是世界上最穩定,最可靠的‘調速器’!任何來自蒸汽機的微小扭矩波動,在它那恐怖的慣性麵前,都會被輕易地抹平,變成最順滑,最穩定的旋轉輸出!”
地麵上的草圖,簡單,卻又充滿了天才的構想。
減震基座、長距皮帶、大質量飛輪。
這三者結合,構成了一套完整而自洽的,將蒸汽的狂野之力,馴化為精密之源的解決方案!
王敬山呆呆地看著地上的草圖,他那顆浸淫了機械原理一輩子的腦袋,在短短幾分鐘內,就完成了對這套係統的可行性驗算。
他發現,這套係統在理論上,竟然真的可行!
這......
這簡直是瘋子才能想出來的計劃!
用最原始的蠻力,去追求最頂尖的精細。
這本身,就是一種“朋克”精神!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王敬山激動得渾身顫抖,他一把搶過秦洛峰手中的鐵條,跪在地上,開始在那張草圖上飛快地進行補充和修改。
“飛輪的材質,必須用鑄鐵,而且要進行動平衡校準,不然高速轉起來它自己就得散架!”
“皮帶需要重新鞣製,用桐油和牛筋混合浸泡,增加韌性和摩擦力!”
“蒸汽機的鍋爐......該死的,鍋爐是最大的問題!這台消防泵的鍋爐早就鏽穿了,我們上哪兒去找一口能承受至少十個標準大氣壓的鍋爐?”
難題,再次擺在了麵前。
秦洛峰卻笑了,他指了指不遠處一堆被帆布蓋著的雜物。
“誰說我們要自己造?”
他走過去,一把扯開帆布,露出下麵一節鏽跡斑斑,但異常厚重的圓柱形金屬。
那是一節火車頭報廢換下來的車軸,但它的旁邊,還靜靜地躺著一個黑乎乎,布滿了鉚釘的橢圓形罐體。
“這是......”
王敬山湊過去,用手敲了敲那罐體,聽著那沉悶厚重的回響,失聲叫道,“準軌蒸汽機車上的高壓儲氣罐?這玩意兒還沒被拉去煉鋼?”
“它原本的用途是儲存壓縮空氣,用於火車的製動係統。”
秦洛峰平靜地說道,“它的設計承壓,是15個標準大氣壓。我們隻需要在上麵加裝一個安全閥和一個壓力表,再給它做一個外部加熱的燃燒室......它,就是我們最完美的鍋爐!”
王敬山徹底不說話了。
他看著秦洛峰,像是在看一個無所不能的神。
在這座別人眼中的“設備墳場”,這個年輕人總能精準地找到最合適的“廢品”,用一種匪夷所思的方式,將它們組合成解決問題的鑰匙。
這已經不是技術了,這是點石成金的魔法!
“總師......您......您到底是什麼人?”
王敬山的聲音裏,帶著一絲敬畏的顫抖。
秦洛峰沒有回答,隻是拍了拍他的肩膀,目光中燃燒著前所未有的火焰。
“我是一個,想讓這片土地上,再也無人敢言‘技不如人’的......中國人。”
這句話,像一道電流,瞬間擊中了王敬山內心最柔軟,也最痛的地方。
他眼眶一紅,不再多問,隻是重重地點了點頭。
“幹!”
一個字,道盡了所有的決心與追隨。
這一天,南鑼鼓巷95號四合院裏,易中海正在為自己重新樹立威信而苦惱,傻柱在食堂裏對著那些新來的“定量勺”唉聲歎氣,秦淮茹在盤算著下個月的開銷......
滿院的雞毛蒜皮,一如往常。
沒有人知道,在他們所鄙夷、所遺忘的那個軋鋼廠後院角落,在一座堆滿了廢銅爛鐵的破敗倉庫裏。
兩個身影,一個年輕,一個蒼老,正像兩隻勤勞的工蟻,開始了一項足以顛覆時代的,偉大的秘密工程。
他們關上了倉庫那扇沉重的大門,用一根槽鋼從內部死死地抵住。
這裏,成為了他們的獨立王國。
他們用一輛破舊的倒騎驢,開始費力地搬運那台老舊的蒸汽機,將它安放在一個遠離希斯母機的獨立地基上。
他們從廢棄的龍門吊上,拆解下最粗壯的鋼索,用簡陋的滑輪組,小心翼翼地吊起那個巨大的儲氣罐,為它設計著燃燒室的結構。
王敬山拿出了他珍藏了幾十年的工具,那些閃爍著寒光的德製鏜刀、鉸刀和絲錐,開始對蒸汽機的氣缸和活塞,進行著修複和研磨。
而秦洛峰,則在昏暗的燈光下,手持鉛筆和角尺,在一張張泛黃的牛皮紙上,繪製著一套套複雜的圖紙——傳動係統的齒輪配比圖,飛輪的鑄造和配重圖,鍋爐的安全閥結構圖......
兩個人,幾乎沒有任何交流。
但他們之間的配合,卻默契到了極致。
一個眼神,一個手勢,對方就能立刻心領神會。
汗水,浸透了他們破舊的工裝。
油汙,爬滿了他們的臉頰和雙手。
他們忘記了時間,忘記了饑餓,忘記了外界的一切。
他們的世界裏,隻剩下鋼鐵的碰撞聲,圖紙的沙沙聲,和彼此沉重而有力的呼吸聲。
這,不是在製造機器。
這,是在舉行一場神聖的儀式。
一場用鋼鐵與火焰,去喚醒沉睡之神的儀式。
夜幕降臨,當秦洛峰和王敬山終於停下來,點亮一盞煤油燈時。
倉庫的中央,已經堆滿了他們從各個角落裏搜集來的“零件”——鏽蝕的鍋爐,開裂的皮帶,巨大的飛輪,斑駁的齒輪......
在昏黃的燈光下,這些冰冷的廢鐵,不再是垃圾。
它們仿佛被注入了靈魂,圍繞在那台德國母機和那台老舊蒸汽機周圍,像是一群即將奔赴戰場的忠誠士兵,等待著將軍的號令。
秦洛峰靠在“盤古”冰冷的床身上,從懷裏掏出兩個已經涼透了的窩頭,遞給王敬山一個。
王敬山接過來,狠狠地咬了一口,看著眼前這番景象,渾濁的老眼中,映著跳動的火光,他咧開嘴,笑了。
“總師,咱們這事要是幹成了,可叫個什麼名堂?”
秦洛峰咀嚼著幹硬的窩頭,目光穿過倉庫的黑暗,仿佛看到了未來那星辰大海般的壯麗景象。
他笑了笑,用一種隻有他們兩人能懂的暗語,輕聲說道:“就叫......‘盤古之心’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