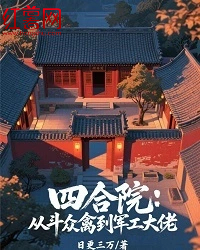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10章
總師!
這兩個字,仿佛擁有穿越時空的魔力,如同一道驚雷,在秦洛峰的靈魂深處轟然炸響!
前世,在戒備森嚴的九院,在國之重器的總裝車間,在每一次技術攻堅勝利的時刻,他聽過無數次這個稱呼。
每一次,都伴隨著崇敬、信任和將國家命運托付於肩的沉重。
他以為,這個稱呼,連同他“盤古”的代號,早已隨著他生命的終結,一同埋葬在了那個世界。
卻沒想到,在1956年這個寒冷的冬日,在一個堆滿了廢銅爛鐵的破敗倉庫裏,從一個衣衫襤褸、滿身酒氣的老工匠口中,再次聽到了這個闊別已久,卻早已刻骨銘心的稱呼。
秦洛峰看著眼前淚流滿麵、身軀挺得筆直的王敬山,心中百感交集。
他知道,王敬山敬的,不是他這個二十歲的年輕人,而是他剛才展現出的,那種超越了時代,代表著工業文明巔峰的“道”!
那是一種共通的語言,是所有頂尖工匠都能心領神會的精神共鳴。
秦洛峰緩緩上前,伸出雙手,用一種不容置疑卻又充滿尊重的力量,將王敬山那依舊敬著禮的手,輕輕地按了下來。
“王師傅,”
秦洛峰的聲音,第一次帶上了一絲前世身為總師的溫和與威嚴,“過去的事,都過去了。現在,沒有中央兵工廠的王技師,隻有一個叫王敬山的老師傅。”
他頓了頓,漆黑的眸子凝視著王敬山,一字一句地說道:“也......沒有總師。隻有一個叫秦洛峰的,一級鉗工。”
王敬山嘴唇顫抖,老淚縱橫,卻執拗地搖著頭:“不!您就是!我王敬山這輩子,沒服過幾個人。當年在漢陽,德國來的專家,美國的顧問,我跟他們比過手藝,贏過,也輸過,但從沒服過!因為我知道,他們的厲害,是厲害在機器上,厲害在圖紙上!”
“可您......可您......”
王敬山激動得有些語無倫次,他指著那把被修複得天衣無縫的千分尺,又指了指秦洛峰,“您就是機器!您就是圖紙!您就是規矩!這門手藝,到了您這兒,就不是術,是道!是通了天的道啊!我王敬山這雙招子還沒瞎,我認得出來!您,擔得起‘總師’這兩個字!”
說完,他竟然後退一步,又要彎腰下拜。
秦洛峰一步上前,死死地扶住了他。
四目相對,秦洛峰從那雙渾濁卻明亮的老眼中,看到了一種名為“信仰”的光芒。
他知道,對於王敬山這樣的人,任何的謙虛和否認,都是一種侮辱。
他長長地吐出一口氣,扶著王敬山的肩膀,鄭重地點了點頭。
“好。”
僅僅一個字。
卻重若千鈞。
從這一刻起,秦洛峰不再僅僅是為了自己在這個時代活下去,他接過的,是王敬山身上那份沉甸甸的,屬於上一個時代頂尖工匠的,不甘與期望。
王敬山笑了,哭著笑了。
他仿佛一個找到了回家路的孩子,又像一個終於可以將手中火炬遞出去的老兵。
他擦了一把臉上的淚水和油汙,指著那台沉睡的希斯母機,聲音裏充滿了壓抑了二十年的激動。
“總師,您看它!‘施耐德’,我給它起的名字。當年,它剛到漢陽的時候,多威風啊!整個廠,就隻有我跟師傅兩個人有資格碰它。用它做出來的炮膛,比德國原廠的還要光滑!可後來......打仗了,廠子西遷,一路顛簸,再後來......就沒人把它當回事了。”
王敬山的臉上,露出了心疼如刀割的表情。
“他們拆它的零件,卸它的電機,最後把它當成一堆廢鐵,扔到了這裏。我求爺爺告奶奶,才把它保了下來,他們說我瘋了,守著一堆廢鐵不放。可我知道,它不是廢鐵!它是咱們中國工業的根!隻要它還在,這口氣,就斷不了!”
秦洛峰靜靜地聽著,他能感受到王敬山話語中那份深沉的悲愴與執著。
他走到那台“施耐德”麵前,伸出手,輕輕地撫摸著那塊刻著“SchiessDefries”的銅質銘牌。
冰冷的觸感,仿佛能傳遞來它穿越半個世紀的孤寂。
“王師傅,”
秦洛峰的聲音平靜而有力,“你說錯了。”
王敬山一愣。
秦洛峰轉過身,目光如炬,掃過這滿倉的鋼鐵遺骸,最後定格在王敬山的臉上。
“它不是根,根,在我們自己的手裏,在我們的大腦裏!”
“從今天起,它也不叫‘施耐德’了。”
秦洛峰從口袋裏掏出那塊擦拭過千分尺的鹿皮,仔仔細細地,將那塊布滿了油汙和鏽跡的德國銘牌,擦拭得鋥亮。
然後,他用手指,在那冰冷的金屬上,一筆一劃地寫下兩個字。
“盤古。”
“盤古開天,造化萬物。”
秦洛峰的聲音,在空曠的倉庫裏回響,帶著一種不容置疑的信念,“從今天起,它就是我們開天辟地的第一把斧子!我們要用它,親手為這個國家,鑄造出一個全新的工業帝國!”
王敬山呆呆地看著那塊銘牌,嘴裏反複咀嚼著“盤古”這兩個字。
他不懂什麼帝國,什麼開天。
但他能聽懂秦洛峰話語中那份吞吐天地的豪情與壯誌!
他隻覺得渾身的血液,都在這一刻被點燃了!
那顆早已被酒精和歲月侵蝕得麻木的心,在二十年後,再一次,為了“工業”這兩個字,瘋狂地跳動起來!
“好!好一個盤古!”
王敬山激動得滿臉通紅,“總師,您下令吧!要我王敬山幹什麼,上刀山,下火海,絕不皺一下眉頭!”
秦洛峰笑了。
他要的,就是這股氣!
“刀山火海還用不著,”他拉過一個木箱,示意王敬山坐下,“我們現在,要先為這具‘盤古’的身體,鑄造一顆全新的‘心臟’。”
說著,秦洛峰閉上眼睛,將腦海中那份《C50型高精度三爪自定心卡盤》的圖紙,憑著記憶,用鉛筆在找來的牛皮紙上,迅速地描繪了出來。
當那張充滿了現代工業設計美感,標注著各種精密公差和複雜結構的圖紙,展現在王敬山麵前時,這位見慣了德國頂級圖紙的老技師,再一次被震驚得無以複加。
“這......這是......”
王敬山的手指,顫抖地撫過圖紙上那獨特的“楔塊螺旋”結構,眼中充滿了癡迷與困惑,“天......巧奪天工!這是誰設計的?這種結構,我聞所未聞!它......它簡直就是一件藝術品!”
“這是我們即將要製造的第一件‘作品’。”
秦洛峰指著圖紙說道,“有了它,‘盤古’才算真正擁有了超越時代的手。王師傅,現在,我們來盤點一下,鑄造這顆‘心臟’,我們還缺什麼。”
接下來的一個小時,這座被遺忘了二十年的倉庫,變成了世界上最頂級的作戰指揮室。
秦洛峰負責提出要求,王敬山負責盤點家底。
“材料,我們需要鉻釩合金鋼,至少是40Cr的級別。”
“難!廠裏隻有給軍工件特批的庫存,我們根本拿不到。不過......”
王敬山眼睛一亮,“咱們腳下這些廢舊的蘇式坦克負重輪的扭杆,我偷偷藏了幾根,那玩意兒的材質,絕對夠勁!”
“很好!第二個,我們需要一台能進行高頻淬火的設備。”
“沒有!”
王敬山回答得斬釘截鐵,“但是,我能用焦炭和鼓風機,給您燒出不比高頻淬火差的滲碳層!”
“好!第三,我們需要高精度的磨床,來加工卡爪的螺旋曲麵。”
“更沒有!”
王敬山搖了搖頭,隨即又挺起了胸膛,“但是,隻要總師您能畫出基準線,我這雙手,就能用最細的油石,給您一微米一微米地磨出來!”
一個又一個難題被提出,一個又一個看似不可能的解決方案被製定。
秦洛峰的心中,豪情萬丈。
他發現,自己最大的收獲,不是這台希斯母機,而是眼前這個倔強、驕傲,卻身懷絕技的老人!
他就像一部活的工業史,能用這個時代最簡陋的條件,去實現自己那個時代最瘋狂的構想!
他們兩人,簡直是天作之合!
然而,當所有的條件都盤點完畢,最後一個,也是最根本的一個難題,擺在了兩人麵前,如同一座無法逾越的大山。
王敬山臉上的興奮慢慢褪去,化為一片凝重。
他指著那台如鋼鐵巨獸般沉睡的“盤古”,聲音幹澀地說道:“總師,材料、工藝,我們都能想辦法解決。但是......它沒有‘心’了。”
“它的驅動電機,是當年專門定製的西門子三相變極多速電機,功率大得嚇人。別說電機早就讓小鬼子給炸了,就算還在,咱們全廠的電網綁在一起,也帶不動它。”
“沒有電,沒有動力,它......終究隻是一堆廢鐵。”
王敬山的聲音裏,充滿了深深的無力感。
這才是困擾了他二十年,讓他最終心死,隻能與酒為伴的根源。
秦洛峰順著他的目光,望向那台巨大的機器。
是啊,沒有動力,再精密的機器,也隻是冰冷的鋼鐵。
他陷入了沉思,大腦飛速地運轉,前世所掌握的無數技術方案,在腦海中一一閃過。
忽然,他的目光,落在了倉庫角落裏,一堆廢棄的消防器材上。
那裏,有一個鏽跡斑斑,但主體完好的東西。
那是一台老舊的,往複式蒸汽機!
是當年用來驅動消防水泵的!
一個在任何人看來,都無比荒謬,甚至堪稱瘋狂的念頭,在秦洛峰的腦海中,轟然成型!
秦洛峰緩緩站起身,走到那台蒸汽機前,用手敲了敲它厚重的缸體,發出一陣沉悶的聲響。
他轉過頭,看著一臉愕然的王敬山,嘴角,勾起了一抹讓整個時代都為之顫抖的笑容。
“誰說......我們一定要用電?”
“王師傅,你聽說過......‘蒸汽朋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