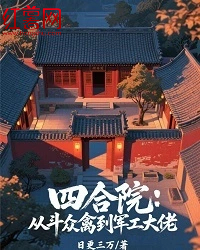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9章
“你要它?”
王老頭沙啞的嗓音裏,帶著一絲嘲弄,更多的卻是一種深藏的審視,“小子,你知道這是什麼嗎?這可不是你家後院的破銅爛鐵。你叫得出它的名字嗎?”
秦洛峰沒有被這突如其來的氣勢所懾,他平靜地迎著王老頭的目光,緩緩吐出幾個字:“德國希斯公司,1938年產,重型精密車床。如果我沒猜錯,這應該是當年德國人賠償給咱們,後來又在戰火中幾經輾轉,才流落到這裏的‘母機’。”
王老頭的瞳孔,劇烈地收縮了一下。
整個倉庫,除了他,已經沒人知道這台機器的來曆了。
這個二十歲出頭的年輕人,是怎麼一眼認出來的?
“好,好眼力。”
王老頭嘿嘿冷笑兩聲,那笑聲裏卻再無半分輕視,“既然你知道它是誰,就該知道,它不是你能碰的。它已經死了,死了快二十年了。你想讓它活過來?憑你?憑你昨天在車間裏銼塊鐵顯擺的那點三腳貓功夫?”
秦洛峰知道,真正的考驗,現在才開始。
這個王老頭,絕非凡人。
他守著這堆“廢鐵”,或許不是在看管,而是在守護。
守護著一個逝去的時代,和那一代工匠最後的尊嚴。
“三腳貓的功夫,能不能成,總要試過才知道。”
秦洛峰不卑不亢地回答。
王老頭站起身,將酒葫蘆往腰間一別。
他雖然身形佝僂,但站直的一瞬間,那股無形的壓迫感,竟比車間主任劉建國還要強上三分。
他走到一個積滿灰塵的工具箱前,從裏麵翻出一個用油布包裹得嚴嚴實實的東西,“啪”的一聲,丟在秦洛峰麵前的木箱上。
“想動它,可以。先過了我這關。”
秦洛峰解開油布,裏麵是一把外形古樸的千分尺,同樣是德國貨,看樣式,比那台希斯母機還要早上幾年。
但這把千分尺的測砧,已經從中斷裂,徹底報廢。
“這是我當學徒時,我師傅傳給我的吃飯家夥。”
王老頭的聲音裏,帶著一絲複雜的情緒,“後來,讓個不長眼的混小子給摔了。測砧斷了,淬火層也毀了,神仙難救。你,要是能把它修好,讓它的精度,恢複到出廠時的水準。那台希斯,你隨便折騰。我老頭子,這條命都算你的!”
“你要是修不好,”
他從懷裏摸出半瓶沒喝完的“汾酒”,放在旁邊,“這半瓶酒,歸你。然後,給我滾出這個倉庫,永遠別再回來!”
一個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一個以信念和尊嚴為賭注的賭局。
修複一把斷裂的精密量具,比從零開始製造一把還要難上百倍!
因為不僅要接續斷裂麵,還要恢複其被破壞的熱處理金相組織和微米級的精度。
秦洛峰看著那把斷裂的千分尺,又看了看王老頭眼中那份夾雜著期盼、挑釁與悲涼的複雜眼神,他忽然明白了。
王老頭不是在刁難他,而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尋找一個答案。
尋找一個,這個時代是否還有人,配得上“工匠”這兩個字的答案。
秦洛峰笑了。
“酒,我不要。”
他將那半瓶汾酒推了回去。
“您的這把尺子,我要修。那台機床,我也要定了。”
“不過,我要加個賭注。”
“哦?”
王老頭挑了挑眉。
秦洛峰的目光,穿過倉庫的塵埃,望向外麵那片火熱的廠區,一字一頓地說道:“如果我修好了它。從今往後,您,王師傅,得聽我的。”
王老頭先是一愣,隨即放聲大笑,笑得前仰後合,眼淚都快流了出來。
“好小子!夠狂!我王敬山這輩子,還沒聽過這麼狂的話!行!我賭了!”
......
與此同時,一號鉗工車間。
易中海陰沉著臉,坐在自己的工位上,麵前的茶水已經涼透。
周圍的工人們都有意無意地避開他,自昨天之後,這位曾經說一不二的八級鉗工,威信已經一落千丈。
傻柱提著個飯盒溜了進來,湊到易中海跟前,壓低聲音道:“一大爺,您聽說了嗎?那姓江的小子,今天沒來車間,跑去後院倉庫撿破爛去了!”
“撿破爛?”
易中海皺了皺眉。
“可不是嘛!”
傻柱一臉幸災樂禍,“劉主任還真就批了他的假,讓他去那堆廢鐵裏鼓搗。我看啊,他就是個銀樣鑞槍頭,昨天露了一手,今天就不知道天高地厚,想去修那些洋古董?他以為他是誰?等著瞧吧,不出三天,他就得灰溜溜地滾回來!”
易中海聞言,臉色稍霽。
他最怕的,是秦洛峰繼續在車間裏,用那神乎其神的技術,一點點蠶食他的威信和地位。
現在秦洛峰自己跑去無人問津的“設備墳場”,在他看來,這無異於自尋死路,自絕於集體。
“哼,年輕人,好高騖遠,終究要栽跟頭。”
易中海端起涼透的茶水喝了一口,心中冷笑,“就讓他去折騰,等他碰一鼻子灰,就知道這紅星軋鋼廠,離了誰都照樣轉!”
......
“設備墳場”內,一場鋼與火的交鋒,正在上演。
秦洛峰沒有急著動手,而是先向王老頭要來了一套繪圖工具。
他將那把斷尺的每一個部件都仔細測量,繪製成圖,甚至連斷裂麵的不規則形狀,都用投影法精確地描繪了出來。
王敬山站在一旁,看著秦洛峰那行雲流水般的繪圖手法,和他圖紙上那無比精準、規範的標注,眼中的輕視,已經徹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凝重。
圖紙,是工程師的語言。
這個年輕人,說的是最純正的“德語”!
接著,秦洛峰開始了他的修複工作。
他沒有用倉庫裏現成的鐵料,而是在一堆廢棄的軸承裏,挑出了一枚滾珠。
他告訴王敬山,這是最好的鉻鋼,其材質,最接近德國貨。
他用王老頭那個小小的、隻用來熱飯的煤爐,搭起了一個簡易的鍛造台。
“叮!叮!叮!”
清脆的敲擊聲,在空曠的倉庫裏回響。
秦洛峰一手持鉗,一手握錘,將那顆燒得通紅的滾珠,在一方小小的鐵砧上,反複地鍛打。
他的每一次落錘,力量、角度都恰到好處,仿佛經過了千百次的計算。
堅硬的滾珠,在他的錘下,竟然如麵團般,被慢慢地塑造成了測砧的雛形。
王敬山的呼吸,已經變得有些粗重。
這手鍛造的功夫,沒有三十年的功力,絕不可能如此隨心所欲!
雛形有了,接下來是熱處理。
退火,消除鍛造應力。
淬火,提升硬度。
回火,增加韌性。
秦洛峰沒有溫度計,沒有儀表。
他判斷火候,隻憑一雙眼睛!
他盯著那在炭火中由紅轉橙,再由橙轉黃的鋼件,在它顏色達到某種微妙的“櫻桃紅”時,猛然夾出,迅速浸入一旁的機油中。
“滋啦——”一聲輕響,白煙升騰。
完美的淬火!
王敬山的手,已經不自覺地握緊了。
他自己就是玩火的祖宗,自然看得出,秦洛峰對火候的把握,已經到了爐火純青,人火合一的境界!
最後,是接續和研磨。
秦洛峰利用斷裂麵天然的不規則形狀,將其製作成了完美的“燕尾榫”。
再利用熱脹冷縮的原理,將新製作的測砧與尺身精準地鑲嵌在一起,嚴絲合縫,渾然天成。
最後的研磨,更是讓王敬山看得眼珠子都快掉了出來。
秦洛峰沒有用砂輪,也沒有用油石。
他找來一塊最平整的鑄鐵板,塗上最細膩的金剛砂和機油,用一種近乎玄妙的“8字研磨法”,對手工修複的尺麵進行最後的精度打磨。
他的動作輕柔而專注,像是在擦拭一件稀世珍寶。
時間,在這一刻仿佛靜止了。
兩個小時後,秦洛峰終於停下了手。
他用一塊鹿皮,將修複好的千分尺擦拭得鋥亮,遞到了已經徹底石化的王敬山麵前。
“王師傅,您看看,行了嗎?”
王敬山顫抖著,接過那把仿佛獲得了新生的千分尺。
斷裂處已經完全看不出痕跡,仿佛它天生就是如此。
他轉動微分筒,那熟悉的、順滑而又帶著一絲阻尼的觸感,讓他熱淚盈眶。
他跑到那台希斯母機前,顫抖著手,用這把修複好的尺子,去測量導軌上一處他早已爛熟於心的磨損點。
屏幕上的讀數,與他記憶中那個由德國工程師親手測出的數據,分毫不差!
甚至,尺子本身的手感,比當年還要順滑、穩定!
王敬山緩緩地抬起頭,看著眼前這個神色平靜的年輕人,渾濁的老眼中,淚水再也抑製不住,奪眶而出。
他輸了。
輸得心服口服,輸得酣暢淋漓!
他沒有輸掉那半瓶汾酒,而是贏回了自己丟失了二十年的東西——一個工匠的,希望!
他猛地抬起手,用那隻滿是老繭和油汙的手,對著秦洛峰,鄭重地敬了一個已經有些不標準的軍禮,聲音哽咽而嘶啞:“前國民政府中央兵工廠,首席技師,王敬山......”
“見過......總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