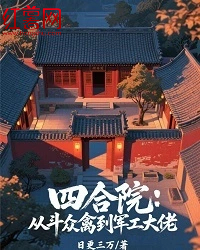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3章
寒風蕭瑟,吹不散院子裏凝固的尷尬氣氛。
一場鬧劇,以賈家婆媳的叩頭求饒和易中海的鐵麵無私收場。
晚飯時分,往日裏總會傳出各家鍋碗瓢盆聲響的四合院,此刻卻安靜得有些過分。
中院,易中海家。
飯桌上擺著一盤窩頭,一碟鹹菜,一碗稀粥。
一大媽看著悶頭吃飯,一言不發,臉色陰沉得能滴出水來的易中海,小心翼翼地開口:“老易,還在為院裏的事煩心呢?”
易中海將筷子重重地拍在桌上,發出“啪”的一聲脆響。
“煩心?我是惡心!”
他咬著後槽牙,聲音從牙縫裏擠出來,“我易中海在院裏幾十年,算計了一輩子,到頭來,竟然被一個黃毛小子給上了一課!烈士家屬......藏得可真深啊!”
他今天丟人丟大了。
本想拿捏秦洛峰,彰顯自己一大爺的威嚴和“公允”,結果卻被對方拿著國家大義當武器,逼得他不得不親手處理自己扶持的賈家,成了秦洛峰立威的墊腳石。
這種被人當槍使,還不得不擺出大義凜然模樣的感覺,比吃了個蒼蠅還難受。
“那......那秦洛峰的工作......”
一大媽擔憂地問。
易中海眼神一寒:“他今天敢拿出烈士證明,就說明他根本沒打算把工作讓出來。這個秦洛峰,已經不是以前那個任人拿捏的軟柿子了,他心裏有主意!”
“那傻柱那邊......”
“哼,”
易中海冷哼一聲,“傻柱就是個棒槌!到現在還以為那工作是他的囊中之物。明天,我得親自去會會這個秦洛峰。房子是烈士家屬的,這工作名額,可未必就非他莫屬!”
......
與此同時,賈家。
屋裏的氣氛更是如同冰窖。
賈張氏躺在床上哼哼唧唧,臉上又紅又腫,一半是自己打的,一半是氣的。
秦淮茹坐在小板凳上,默默地縫補著棒梗的舊衣服,昏暗的燈光下,她那張俏麗的臉龐顯得有些晦暗不明。
“媽,您就別哼了,今天這事,是我們栽了。”
秦淮茹的聲音有些沙啞。
“我就是不甘心!”
賈張氏猛地坐起來,“憑什麼!他一個無父無母的絕戶,憑什麼占著那麼好的房子!現在還成了烈士家屬,以後誰還敢惹他?我們家棒梗怎麼辦?我的乖孫啊!”
秦淮茹停下了手裏的針線活,眼中閃過一絲複雜的情緒。
她也在想,秦洛峰到底是怎麼回事?
一夜之間,仿佛脫胎換骨。
那眼神,那氣勢,根本不像一個二十歲的青年。
特別是他最後說的那句話,“我的耐心和國家的法律,都不是擺設”,至今還回響在她耳邊,讓她心頭發寒。
她忽然意識到,自己以前那種若有若無的示好,那種楚楚可憐的姿態,在這個全新的秦洛峰麵前,恐怕再也起不到任何作用了。
“媽,以後......咱們別去招惹他了。”
秦淮茹低聲說道,“他現在是烈士家屬,有國家護著,我們惹不起。”
“那房子的事就這麼算了?”
賈張氏不甘心地叫道。
秦淮茹的目光投向了窗外,秦洛峰家的方向,漆黑一片,卻仿佛有一頭猛虎蟄伏其中。
她幽幽地歎了口氣:“算了......還能怎麼樣呢?”
......
第二天,天剛蒙蒙亮。
秦洛峰就已經醒來。
係統獎勵的身體素質強化,讓他一掃原主那病怏怏的虛弱感,渾身充滿了力量。
昨晚,他用係統獎勵的錢和票,奢侈地吃了頓飽飯,現在精神十足。
他穿上那身洗得發白的工裝,又仔細地將烈士證明和招工通知等文件貼身放好。
今天,是他去紅星軋鋼廠報到的日子,也是他奪回“鐵飯碗”的決戰之日。
他剛推開門,就看到兩個人影堵在了門口。
正是傻柱和他身後的“軍師”易中海。
傻柱,本名何雨柱,人高馬大,此刻正抱著胳膊,斜著眼睛看秦洛峰,一臉的不耐煩和挑釁。
“秦洛峰,你小子還真要去啊?”
傻柱的語氣充滿了優越感,“一大爺都跟我說了,你那工作,廠裏已經定了給我。你別去自討沒趣了,趕緊把招工通知給我,省得大家麻煩。”
易中海站在一旁,背著手,擺出一副長輩的架勢,語重心長地說道:“秦洛峰啊,不是一大爺說你。你還年輕,身體又不好,去工廠幹體力活,能吃得消嗎?”
“傻柱不一樣,他身強力壯,又是食堂的大師傅,人脈廣,他去頂這個職,以後在廠裏也能罩著你。再說了,傻柱還得接濟秦淮茹她們家,一大家子人指著他呢,你孤身一人,何必非要爭這個名額呢?”
好一番冠冕堂皇的說辭。
看似是為你著想,實則就是讓你為了他們所謂的“大局”,犧牲自己的利益。
若是原主,恐怕在這位德高望重的一大爺和蠻橫的傻柱麵前,三言兩語就被說動,稀裏糊塗地就把關乎身家性命的工作給讓了出去。
但現在,站在他們麵前的,是秦洛峰。
秦洛峰看著這對“父子情深”的組合,差點氣笑了。
“一大爺,我身體好不好,吃不吃得消,就不勞您費心了。”
秦洛峰的語氣很平靜,卻帶著一股不容置疑的堅決。
他看向傻柱,眼神裏帶著一絲憐憫:“還有你,傻柱。誰跟你說這工作是你的?廠領導跟你說的,還是你爹跟你說的?”
“你!”
傻柱被噎了一下,他當然沒接到任何通知,一切都是易中海跟他吹的風。
“我爹媽都是烈士,這個工作名額,是國家和廠裏給我的撫恤!你現在想搶,那就是搶烈士的撫恤!怎麼,昨天賈家搶我房子的教訓,你沒看見?”
秦洛峰的聲音陡然轉冷。
“烈士”兩個字一出,傻柱的氣焰頓時矮了半截。
他蠻橫,但他不傻,昨天賈張氏那下場他還曆曆在目。
易中海的臉色也沉了下來:“秦洛峰,你怎麼說話呢!我們不是那個意思!我們是跟你商量!”
“商量?”
秦洛峰嗤笑一聲,“一大爺,我沒工夫跟你們商量。我現在要去廠裏報到,麻煩你們,讓開。”
“小子,你別給臉不要臉!”
傻柱被秦洛峰的態度激怒了,上前一步,就想動手。
易中海一把拉住了他,對著秦洛峰沉聲道:“秦洛峰,你別以為有烈士證明就能為所欲為!廠裏有廠裏的規矩!你這麼做,是會吃虧的!”
這話裏,已經帶上了濃濃的威脅意味。
秦洛峰卻連眼皮都懶得抬一下,直接從兩人中間的縫隙裏走了過去,連一絲停頓都沒有。
“我的事,我自己做主。吃不吃虧,也用不著您來操心。”
淡淡的聲音傳來,人已經走出了院門。
“嘿!你個小王八蛋!”
傻柱氣得直跳腳,就要追出去。
“回來!”
易中海一把將他拽住,臉色鐵青地看著秦洛峰遠去的背影,眼神陰鷙。
“一大爺,就讓他這麼去了?”
傻柱不甘心地問。
易中海眯了眯眼,冷笑道:“讓他去!我倒要看看,沒有我點頭,他這個職,怎麼入!”
說完,他轉身快步回屋,顯然是去打電話了。
以他八級鉗工的身份,在廠裏,尤其是在生產車間,還是有相當大的話語權的。
......
紅星軋鋼廠。
作為京城最大的鋼鐵企業之一,整個廠區都充滿了那個時代特有的火熱氣息。
高聳的煙囪吐著濃煙,巨大的廠房裏不時傳來機器的轟鳴和金屬的碰撞聲,空氣中彌漫著一股鐵鏽和煤煙混合的味道。
秦洛峰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這股味道,讓他感到莫名的親切。
前世,他就是在無數比這更複雜、更精密的工廠和實驗室裏,度過了自己的一生。
他輕車熟路地找到了廠辦公樓,敲響了“人事科”的門。
開門的是一個戴著眼鏡,四十歲左右的中年幹部,胸口的口袋裏插著一支鋼筆,看到秦洛峰,推了推眼鏡,公式化地問道:“同誌,你有什麼事?”
“您好,我是來辦理入職的。”
秦洛峰不卑不亢地說道,同時將自己的全套文件遞了過去。
那幹部接過文件,狐疑地打量了秦洛峰一眼。
當他看到那份鮮紅的《革命烈士證明書》時,手明顯頓了一下,臉上的表情也從公式化,轉為了一絲肅然。
他仔仔細細地核對著招工通知和秦洛峰的身份信息,確認無誤後,點了點頭,態度也溫和了不少:“原來是烈士子弟,秦洛峰同誌,你好。我是人事科的幹事,我叫王泉。”
“王幹事您好。”
“文件都對得上,你等一下,我給你辦手續,辦好了你就可以去財務科領你的工牌、飯票,然後直接去鉗工車間找車間主任報道。”
王泉說著,便從抽屜裏拿出表格,準備填寫。
秦洛峰心中一鬆,看來易中海的手,還沒那麼長,能伸到人事科來。
然而,他這個念頭剛剛閃過——辦公室的門,被人“砰”的一聲推開了。
一個挺著啤酒肚,梳著油頭,滿麵紅光的胖子,大搖大擺地走了進來,他看都沒看秦洛峰,直接對王泉說道:“小王,手頭的事先放一放。”
王泉一看到來人,立刻從椅子上站了起來,恭敬地喊道:“李副廠長,您怎麼來了?”
李副廠長?
秦洛峰的目光一凝,心中頓時警惕起來。
這位,就是整個軋鋼廠裏最好大喜功、最喜歡拉幫結派的李副廠長,李愛民!
李副廠長背著手,慢悠悠地走到辦公桌前,瞥了一眼桌上的文件,然後將目光轉向秦洛峰,皮笑肉不笑地說道:“你就是秦洛峰?”
“是我。”
秦洛峰平靜地回答。
李副廠長用一種審視的目光上下打量著秦洛峰,慢條斯理地說道:“哦,關於你這個鉗工的名額......我剛剛接到車間易中海老師傅的電話,他說,院裏經過一致商議,已經有了新的人選安排。”
他頓了頓,語氣中帶著一種不容置疑的傲慢:“所以,你這個入職手續,我看......就先不要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