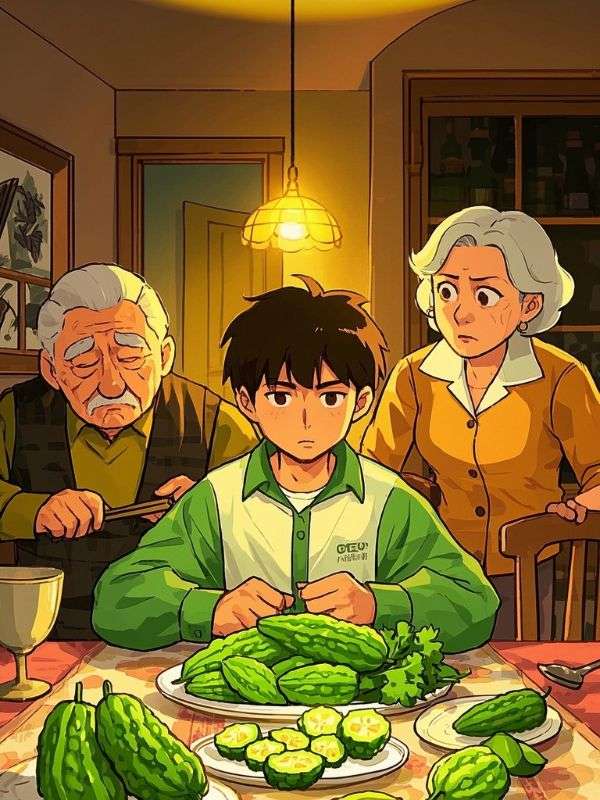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4
我決定先從陳立生那家公司查起。這種老牌企業,隻要存在得夠久,互聯網上總會留下痕跡。我翻找著本地新聞網站的陳年舊檔,把時間軸拉回到十年、十五年前。
終於,在社會新聞版塊一個不起眼的角落,一條被塵封的報道映入我的眼簾。
《本市富商陳立生獨女郊遊墜崖,不幸身亡》
報道上的黑白照片有些模糊。
獨生女,陳念,十年前,墜崖,身亡。
我盯著“獨生女已故”幾個字,腦子裏嗡嗡作響。如果陳立生的女兒十年前就死了,那張薇是誰?那條帶血的裙子,又算怎麼回事?
我關掉電腦,後背的冷汗已經浸濕了衣服。
新聞裏提到了陳家的舊址,我按著地址找了過去。巷子很深,陽光照不透,空氣裏一股子潮濕的黴味。巷口有家開了幾十年的雜貨鋪,老板是個滿頭銀發的老奶奶,正戴著老花鏡在劈裏啪啦地撥算盤。
我買了瓶水,擰開喝了一口。
“奶奶,問您個事兒。以前住這兒有姓陳的嗎?家裏有個姑娘。”
“哦,老陳家啊。”老奶奶放下算盤,抬起頭,“他家女兒叫念念,多好的孩子,學習好,又懂事,可惜了......”她長長地歎了口氣。
“您還有她的照片嗎?我是她以前的同學,好多年沒見了,怪想她的。”
“有!怎麼沒有!”老奶奶來了興致,顫巍巍地從櫃台下的舊餅幹盒裏,翻出一張發黃的集體照,“當年社區活動拍的。你看,這個紮馬尾辮,笑得最甜的,就是念念。”
我接過照片,心臟幾乎要從喉嚨裏跳出來。
照片上的女孩眉眼彎彎,笑容很幹淨,和張薇有六七分相像。
可那種從裏到外的明亮勁兒,是張薇臉上那種戾氣和算計模仿不來的。
最關鍵的是——照片上的陳念,眉角光潔,沒有疤。
我跟老奶奶道了謝,幾乎是跑著離開那條小巷。
張薇的社交動態裏,提過一個地方,說那裏很安靜。
一個騙子,需要安靜的地方做什麼?
我打了輛車,直接報了郊區那片墓園的名字。
黃昏,天邊的顏色有點瘮人。
我隔著老遠就瞧見了張薇的背影,她一個人站在一排墓碑前,手裏拿著一束白菊花,背影竟有些蕭索。
她在祭奠誰?
我借著墓碑的遮擋,一點點湊過去。
墓碑上就兩個字:陳念。
旁邊貼著的黑白小照片,和老奶奶給我看的那張一模一樣。
一個荒唐到可笑的念頭在我腦子裏炸開。
就在這時,口袋裏的手機劇烈震動起來。
陌生號碼。
我按下接聽鍵,一個字還沒說出口。
“照片你看到了吧。”
是李月,那個繼母。她的聲音沒什麼溫度。
“給你發短信的人是我。林瀟小姐,你很聰明,應該也猜到一些事了。”
她停頓了一下。
“你的雇主張薇,是陳念當年最好的朋友。”
“我有理由懷疑——”
她的聲音壓得很低,字字句句都像淬了毒的刀鋒,順著聽筒鑽進我的耳朵裏。
“十年前,就是她,把我那個繼女,親手推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