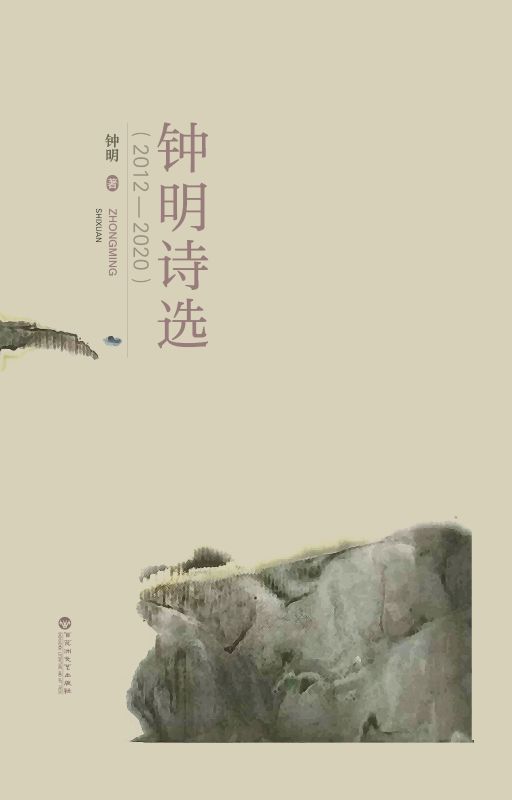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序:古典味與民族風
張德明
近幾年來,鐘明的詩歌創作一直保持在一個高水平上,而且她還始終以執著的探索姿態,努力拓展著屬於自己獨有的藝術領地。她的詩用語講究,形式獨特,詩行之間的情緒、節奏和意義處理得較為巧妙,閱讀這些詩章,自覺有一種別樣的情感波瀾和精神氣息在激蕩著你,將你默默浸染,使你深受陶冶,讓你時時刻刻心為所動情為所牽。我最看重的是,鐘明通過自我的孜孜探求,逐漸煉出一種在當代詩壇有別於常人的、頗具個人性和藝術辨識度的詩歌樣式,其中鮮明顯露出的古典韻味與民族風格,尤其讓人眼前一亮,心生驚喜。我們不禁要追問的是,鐘明詩歌中的古典韻味和民族風格是如何形成的?這種獨特的藝術氣質在當代詩歌創作中又有著怎樣不俗的意義和價值呢?
中國新詩誕生至今,已逾百年時光。但百餘年來,中國新詩的創作始終擺脫不了西方詩歌的影子,拿梁實秋的話來說,中國新詩很多時候正是“用中文寫的外國詩”(《新詩的格調及其他》)。事實上,中國自古就是詩之大國,有著異常豐富的詩歌美學資源,新詩如何有效地繼承古典詩歌美學傳統,讓其更具中國特色和民族個性,這是新詩誕生以來一代又一代的詩人都在多方探尋方案但始終沒有找到良策的重大詩學問題。從這個角度來說,鐘明的藝術探路是值得肯定的,也是極有價值的。她的詩歌有特定的表達路徑,有古典味道豐厚的韻式和氣脈,同時也有民族色彩鮮明的意象群落和語言譜係,為中國新詩有效承襲古典詩歌傳統且更能凸顯中國氣派和民族風格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樣板,因而值得我們細致分析。
鐘明詩歌有一種獨特的文體形式,我稱之為“對話體”,通過與古典詩歌對話、與文化遺產對話、與人文傳統對話,鐘明將自我對中華民族的曆史、文化和傳統的深刻領悟藝術地彰顯出來。例如,在組詩《遊弋詩經》中,通過與《詩經》對話,詩人重返曆史空間之中,細察先民的生命形態和情感形式,並用現代人的生命趣味和精神立場照亮了古人的生命,從而對“詩經文化”做了較為新穎的美學闡釋。《靜女》一詩如此寫來:
春光。——脫去衣裳。
脫去血色。
脫去筋骨。
沒入光芒裏。
我愛的人,你還在那片喧囂中等待我尚未燃燒殆盡的
彤管嗎?
夕光下手握的夜色,都碎了。
你看吧,我影淩亂,
我足,靜如
其姝。
詩中所述的“靜女”顯然是一位有獨立精神意識的現代人,但也並沒失去作為一位癡迷於愛情的古典女子所具有的高潔品質。“彤管”“夕光”“影淩亂”等語詞在詩中的聯袂出場,更是強化了守護愛情的這個女性所存身的古典化場域。詩中的“靜女”既是現代的又是傳統的,既有當代風采也有古典氣息,她就是傳統與現代的完美結合。其實,美好的人倫情感總是超越時空的,對於電光石火般的愛情來說,哪有什麼傳統和現代的嚴格分野?對於《詩經》來說也一樣,真正的經典是不受時空局限的。換句話說,《詩經》中涓涓流淌的古典韻味,是可以與當下社會形成即時的對話與溝通的,通過對話與溝通,我們能發現傳統文化的現代意義,也能對其中光芒熠耀的古典韻味,生出新的理解與認知。因為與《詩經》的多角度對話,鐘明詩歌的古典韻味也得以呈現出來。
組詩《瓷質的宿命》,是鐘明對景德鎮瓷器進行的係統的詩化演繹,體現著詩人對民族文化遺產的細致審視和個性化認知,由此也折射出其詩歌所攜帶的某種古典意蘊。該組詩由20首短詩構成,從不同層麵敞現了景德鎮瓷器之美,同時也將每一樣瓷器中內蘊的意義和精神揭示出來。如《素三彩》一詩:
遠山近土,以墨勾皴。
那枝花那枚葉在時光的玉裏。
發藝術的芽。素,以鉛華的能量,盡洗鉛華。
初夏粉綠,
蛙聲漸黃,
越鳴越沉的禾田上,徹響村簫社鼓。
說,滋養一個家,一條溪水。
說一個老去的村莊和一個
越來越古老的國度。
要讓那水、火、土的愛恨情仇,
糾結成章。蟬聯,源遠流長。
她願素顏哀玉,不經意路人的目光。
不在意深沉、淺淡,或潔或臟。
以素麵—對煩囂,
以沉寂—對流淌。
那雙空靈的手,千年之外淩空而下,驀然攥緊了
所有饑渴的目光。
在瓷器之中,以紫、黃、綠三色繪成花紋的,稱素三彩。詩人麵對此瓷器,大膽展開想象的翅膀,用具體生動的意象描摹出意趣生動的人間情景,藝術地展示了素三彩之美之妙。因而緊扣景德鎮瓷器這一民族文化遺產來表現,詩行之中所蘊蓄的古典韻味也是較為豐足的。
鐘明詩歌的民族風格也是很突出的,這既得益於她對富有中國特色的語言、意象等都有著較為精深的了悟,也得益於她對古典戲曲形式的熟稔和心領神會。鐘明詩歌中的語言選擇和意象取用,都呈顯古意古韻,這在上麵的文字中我們已經能體察到。同時,鐘明詩歌中流溢著惹人心醉的戲曲調式,這種戲曲腔特別令人著迷。隨便舉一例,就可清晰睹見那撩人心弦的古典戲曲韻式,如組詩《此為春酒》之《金秋(秋)》一詩:
年初孵出的雞崽都已開始下蛋了。
我隨同月色垂下天井,
又高又靜。
一地的稻禾,隻等開鐮。你不會想到,山裏熟悉的草木小獸,
有幾許已成孤本。
柿子在山坡上靜靜地熟。種子有種子延續的套路。
阿婆還是喜歡手工製作的東西,
還是處處講個節禮。
阿爺歎茶,
亨葵及菽,
時而,還是惹來狐仙留置祠堂,惹老尼絮叨……
“七月鳴,八月載績。
載玄載黃,我朱孔陽。”那玉,千百年來都是這樣子地光燦,
這樣子地老,哦……
秋嘗吧,秋嘗。嗟我田者,嗟我農夫。
短句和長句的錯落編排,文言語和白話語的相互夾雜,語氣歎詞的時而出場,都讓人領略到元明戲曲的藝術風味。鐘明的詩歌有耐人品嚼的內在韻味,有如煙繚繞的情緒氛圍,有具有神秘感和光亮感的精神氣息,顯示出具有本土特色的民族個性。這些藝術特征的形成,或許與其詩歌嫋嫋不絕的古典戲曲味是密切相關的。
某種程度上,退休在家專事詩歌的詩人鐘明,而今已經進入了一種可貴的專業寫作狀態。她不盲目跟風,不迎合世俗,而是默默探覓著屬於自己的、有價值的藝術之路,悄然創作出了一批具有鮮明的古典味和民族風的詩歌作品。在過於喧嘩的當代詩壇,鐘明的默然堅守、獨立創作姿態,是特別值得尊敬的,由此磨煉出的藝術作品,自然會具有值得稱道的美學價值。
張德明,文學博士,嶺南師範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教授,南方詩歌研究中心主任,西南大學中國詩學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全國中文核心期刊評審專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廣東省作家協會首屆簽約評論家。已出版多部學術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