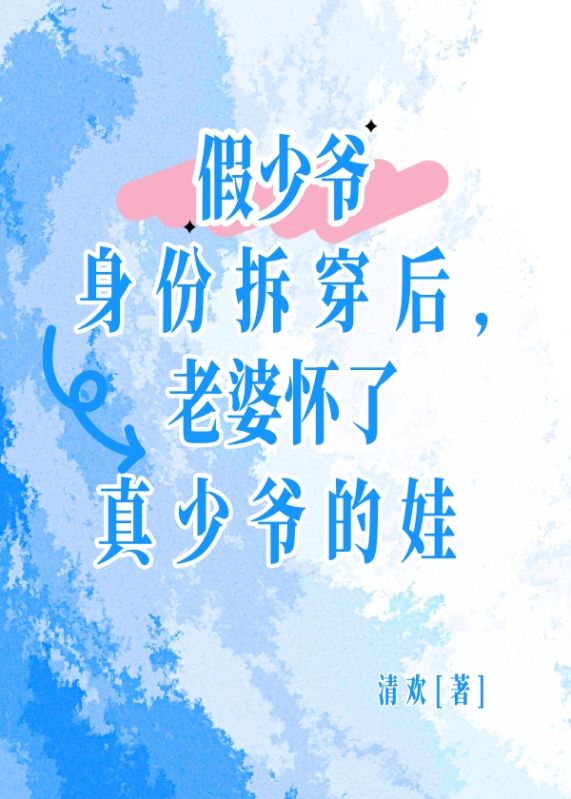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1章
我是豪門假少爺,被趕出家門後以開出租車為生。
老婆嫌我廢物與真少爺廝混在一起。
更是在偷情時將丈母娘鎖在了閉塞的雜貨間。
等我趕回家時已經回天乏力,丈母娘被活活熱死。
我悲痛地給老婆打去電話,她卻認為我在撒謊。
得意洋洋地表示:“我已經懷孕了,你不過是個鳩占鵲巢的假貨,更是個不育的太監,就別妨礙我攀高枝了。”
可惜她不知道,丈母娘真的死了,不孕的也是她。
......
跑完出租車回家後,雜貨間裏彌漫出臭味。
我打開門鎖,發現了丈母娘的屍體。
屍體已經發臭了,又僵又硬,隻餘一雙眼睛瞪得嚇人,丈母娘被活活熱死,死不瞑目。
我又驚又懼,強忍著悲傷將她的眼睛閉合,又踉蹌著跑到臥室,找我的老婆白心禾質問。
她不是說丈母娘已經離開了嗎,為什麼她最後死在了雜貨間。
推開屋門,濃重的石楠花味伴著煙味撲鼻而來,我被嗆得睜不開眼,連連咳嗽。
看清屋內情形後,我臉色變得鐵青。
床上一片狼藉,白色的床單上斑痕塊塊,一看就知道這裏曾經發生過多麼激烈的情事。
我的睡衣被翻出來剪爛在地,旁邊是一件被蹂躪的不成樣子的女士情趣睡衣。
白心禾,你竟然如此對我!
我胸腔劇烈起伏,心中恨意鋪天蓋地。
腦海裏大致推測了事情真相,丈母娘到我家時碰上白心禾偷情。
勸告不成,白心禾幹脆將她鎖在了雜貨間,最後丈母娘被活活熱死!
我顫抖著撥通白心禾的電話。
依然不敢相信她會如此惡毒,竟然能害死親媽。
電話響了很久才被接通,她的嗓音帶著一絲沙啞:“什麼事?”
我冷聲質問:“你偷情的時候想過被你鎖在雜貨間的親媽嗎?她被活活熱死了!”
我赤紅著雙眼,歇斯裏底大喊,白心禾卻沉默了很久,久到我都以為她掛了電話。
心中火氣更甚,我才想重新打給她,便猝不及防地聽見了女人嬌媚的驚呼。
“輕點,電話還沒掛呢。”
“沒掛更好,這樣更刺激。”
低啞的男聲一響起,我就認出了這是真少爺謝承明的聲音。
我渾身血液凝固,呆在原地。
電話裏,不堪入耳的聲音還在繼續。
我的心臟好像被一隻無形的大手攥得發緊,疼得要死。
白心禾,竟然如此不知廉恥。
一陣急喘後,白心禾的嗓音更加沙啞,她渾不在意地開口:“喂,你還在嗎,剛才你說什麼?我沒聽見,再說一遍。”
我氣得要死,頸間青筋暴起。
“我說媽死了。”
死死地攥緊手機,我咬牙切齒擠出一句話。
“謝淮川,你有病吧。你媽才死了!”
白心禾猝不及防對我破口大罵,她不相信我。
我深吸一口氣,直接拍了丈母娘的遺照給她發過去。
她卻更生氣了:“謝淮川,你好端端的發什麼病,詛咒我媽死了不算還給她p遺照!”
“果然是不知身世的野種,心思惡毒。”
登時,我渾身氣血逆流。
心裏一直繃著的名為理智的弦斷了,再也控製不住心中的怒火,與她質問。
“白心禾,我跑車的時候告訴過你,媽來了。那時你恐怕在和謝承明廝混吧。”
提起他們的醜事,想起臥室內不堪的情形,怒氣上腦,我幾乎要被氣的暈過去。
“後來你告訴我媽走了,可事實是她被你鎖在雜貨間,活活熱死!死不瞑目!”
說到這兒,我恨的一拳狠狠砸在門框上。
想起早上我送白心禾到公司時,謝承明非說她忘帶了一份重要的文件。
他故意將五百元現金灑落一地,要我當司機載他和白心禾回我家取。
我不想受辱便拒絕了,可耐不過白心禾淚眼朦朧的哀求。
她說現在是打車高峰期,打不到車。
又在我耳邊低聲分析,謝承明擺明了想羞辱我,如果我不接受,她害怕在公司會受到更多折磨。
為了她,我屈服了。
在謝承明戲謔的眼神中彎腰,撿起了那五百元。
當時我一心想著為了白心禾,忍一時風平浪靜。
卻不想我親自開車將他們送上了我的床,親手給自己戴上了一頂綠帽子。
後來丈母娘給我發消息說到了我家的時候,我正在跑車沒有收到。
再打回去的時候卻怎麼也打不通電話。
想到那段時間,丈母娘應該會和白心禾打過照麵,於是我打給她確認丈母娘的安全,卻被告知丈母娘已經離開。
我想丈母娘可能是在忙工作,才沒有接到我的電話。
卻怎麼也沒想到,丈母娘是永遠離開了人世。
“白心禾,你不覺得你該為媽的死負責嗎?”
我的語氣都在顫抖。
如果不是白心禾的錯誤消息,我或許會早些發現丈母娘的異常,沒準她就不會死了。
“嗬嗬。”
沒等來白心禾的愧疚,謝承明懶洋洋地輕笑出聲。
我清晰地聽見他的嘲諷:“做了十幾年的假少爺,別的沒學到,豪門醃臢倒是學了十成十。”
“心禾,你還沒聽出來嗎。謝淮川爭風吃醋呢,他已經知道咱們的事了。”
我冷笑:“你們在我房間留下了什麼臟東西自己心裏清楚,我再不知道你們的醜事,就真成烏龜王八蛋了!”
“你不是烏龜王八蛋嗎?”
白心禾接過話茬,輕飄飄地嘲諷:“謝淮川,你要是有膽來找我們幹仗,我還敬你是條漢子。可你卻編造謊言詛咒我媽,真是上不了台麵。”
她的語氣中滿是嫌棄。
我氣得火冒三丈。
白心禾也不想想我有什麼理由編造丈母娘去世的謊言。
“謝淮川,事已至此,我也不想瞞了。我和承明在一起了,我已經懷了他的孩子。”
“你沒有生育能力,願意當沒根的太監,我卻想生個自己的孩子。你就別妨礙我攀高枝了,找個時間離婚吧。”
白心禾給我下了最後的通牒,尖酸刻薄的樣子讓我陌生,我心裏頓時五味雜陳。
又氣又震驚。
其實不能生育的人一直是她。
當初我和白心禾結婚三年都沒有孩子。
養父母對她很不滿,經常用話刺她。
養母更是毫不避諱地給我相看別的女孩兒。
為了不讓白心禾受委屈,我才弄了一張假報告,告訴他們是我不能生育。
至此,養父母才重新對白心禾和顏悅色,直至我假少爺的身份被拆穿。
所以,白心禾怎麼會懷孕呢?
“心禾才檢查出來懷孕,金貴的很,暫時不能回你那個狗窩了,過些日子再回去和你離婚,便宜你了。”
謝承明恩賞似地開口,我氣急反笑:“好啊。我看你們能生出個什麼東西!”
“白心禾什麼時候和我離婚都沒關係,但是她現在必須回來和我處理媽的喪事!”
白心禾笑了:“謝淮川,還不死心呢?別費力氣詛咒我媽了,你說的話我一個字都不信!”
她毫不猶豫地掛斷了電話。
我再打過去的時候顯示被拉黑。
丈母娘的遺體還在雜貨間,夏天溫度很高,發酵的臭味逐漸飄到臥室。
沒有辦法,我隻能聯係火葬場,先把丈母娘火化。
走出火葬場的時候,我手上多了個黑盒子。
抱著它,我有些恍惚。
在成為我的丈母娘之前,她是我家的保姆。
我八歲被謝家收養到如今,丈母娘整整照顧了我十八年。
假少爺身份被拆穿後,身邊的人都對我退避三舍,更有甚者以辱我取樂時,丈母娘也是唯一還肯對我好的人。
對我的關懷甚至更甚從前,在我心裏她早就與我的親媽無異。
可是她就這麼沒了,變成一捧灰,棲息在這小小的盒子裏。
眼眶驀然一酸,我開車回到了謝家。
丈母娘為什麼會被鎖在雜貨間,活活熱死,白心禾應該給我一個交代。
我到謝家時,他們正在吃飯。
隨著我的進入,潔白的地板上頓時多了一排臟腳印。
對此,我曾經的養母明晃晃的表示出厭惡:“學了這些年的規矩都到了狗肚子裏,終歸是上不了台麵。”
她嫌棄地捂住鼻子,喚道:“劉媽,把地拖一下。”
劉媽,劉秀英,我丈母娘的名字。
我鼻尖一酸,死死忍住了淚意。
以往隻要養母一呼喊,丈母娘都會第一時間出現為她解決各種問題。
可如今她卻靜靜躺在小盒子裏,再也不會出現了。
養母連連叫了三聲,都無人應答,她臉上閃過不耐。
在她再度開口前,我沙啞開口:“別叫了,劉媽在這兒。”
我指了指手上的黑盒子。
養母臉上的表情僵住了,驚恐盯著我手上的骨灰盒,顯然她已經認出來了這是什麼。
她大怒:“謝淮川,你帶著骨灰盒來謝家幹嘛,滾出去!”
我無動於衷。
白心禾貼心地為她倒了杯涼茶,討好道:“媽,您別怕。骨灰盒是假帶,謝淮川在做戲。”
見她如此信誓旦旦,養母有幾分動搖。
謝承明又吊兒郎當地敘述了之前發生的事。
在他們嘴裏這一切都不過是我和丈母娘聯手上演一出假死的戲碼。
白心禾一邊貼心服侍養母喝茶一邊討伐丈母娘:“我媽也是,一把年紀了,還這麼不懂事,一點忌諱不懂。媽,您放心,我回頭好好說她。”
我苦笑著搖頭:“白心禾,你沒機會了,你為什麼就是不肯相信媽真的死了呢?”
我紅著眼眶,直勾勾地盯著白心禾。
“今天你聯係上過媽嗎?你確定媽現在安全嗎?”
許是心虛,她打了一個冷戰,不小心摔了茶蓋。
不給她反應的時間,我步步緊逼。
“媽又為什麼要和我假死作戲,她的假死對我們有好處嗎?”
“你真的不知道嗎?在你和謝承明偷情的時候,媽被鎖在閉塞的雜貨間活活熱死!”
隨著我的步步逼近,白心禾眼裏終於閃過動搖,臉色也一寸寸變白。
最後我將骨灰盒放大在她眼前的時候,她的臉色已經徹底蒼白如紙。
目光緊緊黏在骨灰盒上,不由自主地接過它,喃喃道:“我媽真的死了嗎?”
事實已經擺在她的眼前,白心禾依然不想承認。
我輕笑反問:“你說呢?”
她呆住了,少頃,淚珠傾斜而下。
見她痛苦,我心裏並不鬆快。
如果可以,我情願接受白心禾出軌一千次,一萬次,隻要丈母娘平安無事就好。
“夠了,真當我家當墓地了,想哭喪滾出去!”
養父驀地發火,將筷子重重拍在桌子上,喚回了白心禾的神誌。
她反應過來卻第一時間將骨灰盒塞回了我懷裏,對養父小心翼翼地解釋:“爸,對不起。”
見此,我心中悲痛,為自己,也為丈母娘不值。
白心禾,涼薄如斯。
“爸媽,心禾,你們不要被謝淮川騙了,劉媽沒有死。”
謝承明突然出聲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